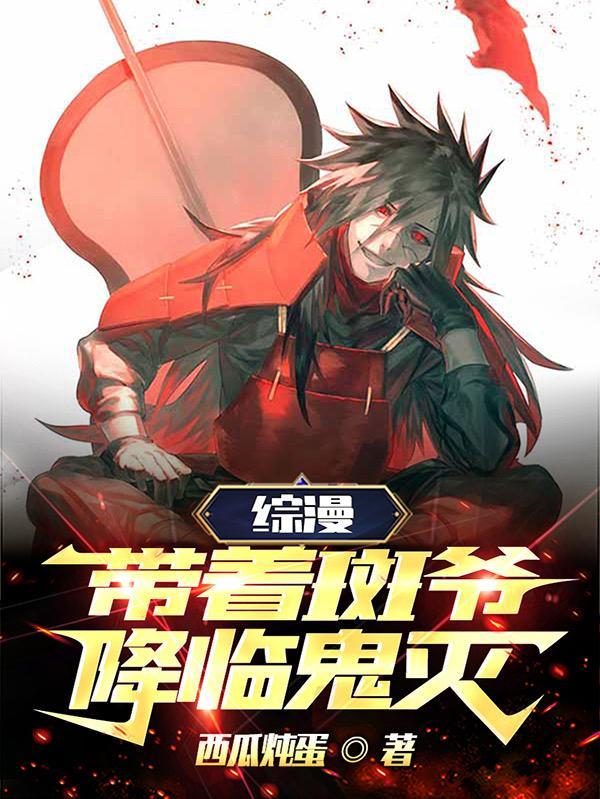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宋朝大官人 > 第一千零八十八章 考题商定(第1页)
第一千零八十八章 考题商定(第1页)
虽有人不满,但却无人敢反对。宁得罪天下小人,切莫得罪陈初六,在这件事上,无论清流不清流,都变得越来越务实起来。
陈初六微微颔首,看来大家都同意了,便又道:「衡文之事,将来还可以缓缓再议。策问定其去留,考完之後,先审策问就是。」
众人点了点头,又议了许久,方才退回各自的房中。浦城章丶晏殊丶陈初六则是留了下来,还要定考题。
浦城章拈须道:「知应,这次贡举改动颇大,虽然提前三个月通晓天下士子,可那是冬日,有些人收不到消息。故而这次出题,万不可太难了。」
陈初六点头道:「策问首当验其心术丶其次考其学识,小题亦可大做。下官这里,倒是有几个题目,还请二位学士过目。」
浦城章丶晏殊相视一眼,便看得陈初六拿了一张纸来,上面写着七个题目。看过之後,晏殊嘀咕道:「诸子之言,考庄子丶吕氏春秋,这两道皆与经合拢,凡熟读经典的人,都应当知道。哪怕不知道,也能站在儒门的立场,写出一篇论来。」
浦城章疑惑道:「那这与经义之论有什麽区别?」
陈初六回到:「区别不大,但题中有一个要求,考生需联系实际,将题中内容结合起来写策问。」
浦城章则又是看向三篇时事道:「近来时事之中议论最多的,无非是郭皇后之废丶吕相之辞丶西凉之叛,为何这三件事,时事之中一件也没有?」
陈初六擦了擦汗,晏殊在一旁解释道:「浦学士,时事历来要避讳,这三件事朝中早已有了定论,还让士子来议论,略有不妥。」
浦城章一想,点头认可了,陈初六这时又道:「下官选的时事,一是淮盐之弊丶二是西域诸国之进贡丶三是节减冗兵冗费之策。」
晏殊笑道:「这几件事,关乎财用四夷,皆是军国大事。但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本官以为甚为妥切。只是这史策,却是难了,本官读书这麽久,也不敢说答得多好。」
陈初六笑了起来,想要开窗透气,就得说要把房顶掀开,这办法屡试不爽,他又道:「那下官再改一改?二位学士有何建议,下官都听你们的。」
於是三人又将这考题敲定下来了,写在了一张纸上,提请御批。浦城章身为主考,也只能在这时出一次贡院,亲自将考题呈上去。
大宋景佑元年,礼部试考题如下:
头场,策七题,任选三道答之,时务必选一道。
题一,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古之道术有在於是者。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以实事求是,辩儒道之异。
题二,《吕览》有言: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匹夫徒步不能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试问何法可取,以仁义之术教化百姓?
题三,《史记》所缺,褚少孙补之。诸侯列为世家,宜矣,而孔子亦次其间,其义安在?
题四,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於志。」郑樵以史志不备,乃作《通志》二十,略可详言其得失。
题五,淮南盐积伤民策。
题六,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西域诸国称臣,安抚四夷策。
题七,浮费弥广,削减冗积策。
次场,诗一首,赋一篇。
《房心为明堂赋》
《和气致祥诗》
三场,论一篇。
《积善成德论》
转眼到了临近考试的日子,天气放晴,街上三三两两的士子,聚在一起晒太阳,顺道去大相国寺求签问卦,卜得一个好兆头。
这时徐良骏丶何健京也是到了,显得意气风发,这二人搀着这一位老者,这人乃是当年叱咤风云的押题王穆修,也是陈初六将四为诗社托付的一人。
穆修不押题已经多年了,离开官场之後,消息不甚灵通。这次来汴京,许是他最後一次来了,也是最後一次将自己辅导过的士子,送入科场。
这次徐良骏丶何健京乃是名声在外的,早在太原府时,这两个人就跟着陈初六写文章,常列於陈初六的名字之下。这两个人,被民间士子视作陈初六的关门弟子。在太原府历练多年回来,更是将学问积淀得十分深厚。
还有两人人,也是呼声很高。一人是山东青州张唐卿,字希元,以孝名闻天下。还有一人是庐州杨察,字隐甫,官宦之後,以文章声名远播。
大相国寺,荷花池旁,徐良骏看着池子里的鲤鱼,投下一枚铜钱,摇头道:「这鱼怎麽会叼铜钱?池中这麽多钱,都让寺里的僧人吃了。」
穆修在一旁道:「信则有,不信则无。不过,你们两人跟着陈知应这麽多年,应当摸清了他的秉性,就算是没有面授机宜,也该能猜到题才对。」
何健京也将一枚铜钱丢入池中,鲤鱼非但不叼,反而受惊一哄而散。何健京脸色失望地道:「去了几次先生府上,连门都没进去。」
穆修笑道:「你们这时候去,当然进不去。你先生不怕非议,是怕你们受到非议。本来能高中的,去了之後,大家这麽一传,就只能让你们低低过了。高中与低中看似差不多,却差之千里。想要爬到一个位置,十年的差别都弥补不了。」
「陈善修也要考,他是先生的亲弟弟,在家里为何就没问题?」
「他是亲弟弟,大家都是知道的,这反而无妨。何况锁厅试与春闱不一般,那是吏部主持。」
「听穆先生的意思,这次我们二人,一定能中?」
「一定能中,诗社里的人,这次能中进士的,不下二十人。若真是这样,将来四为诗社又会令世人趋之若鹜。」穆修笑着回到,这个时候,当然是只能说吉利话了,但徐良骏丶何健京实力还是有的,他又道:
「这次的张唐卿丶杨察,名声虽望,但其实难副。抵京这些士子中,能与你们争的,老夫尚未看到,剩下的只看考场之上了。」
「若说谁与你们有一争之力的,只有两人。徐嘉志长孙徐翰海,徐嘉志深得知应事功之精髓,传之其长孙,徐翰海定是能通实务的。还有一人,便是柳景庄,才华实为士子中的第一。此人屡试不第,若是能痛定思痛,安心读书,定是无人能比。」
「柳景庄,可惜他音讯全无,现在也不知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