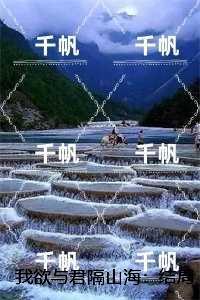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驯服 > 第19章(第3页)
第19章(第3页)
但这只是逢场作戏。
我晓得她只是在做给我看。她不过是一只被驯服的猫,那个男人带来的“快乐”,她就要离不开了。
我也在作戏。父子俩已经没了敌意,李猛叫我们握手言欢。我犯上的欲望他晓得,他分享的怪癖我晓得,只有妈妈什么也不晓得。
所以张亮平回了家,我们又过上老生活,装作一切都没有变。
李猛一伙人照旧,偶尔晚上来做客。
他告诉刘璐他没有药了,但她败倒在他身下,只说别给她丈夫现。
这是感情上的报复,妈妈拿这一点自持,但我参与了每晚的做客,领教了她自我的催眠。
在刘璐心里,儿子一无所知,还当她是那个冰山小姐。
但是她在每个撅起屁股的晚上,那生育我的肉囊里,都会由我补上一点慰藉。
她更不晓得,张亮平是故意挑时间晚归,达成被她背叛的快感。
所有男人都有了默契,各取所需。
只有小妇人以为自己藏得好,挂着冷冷清清的面子,做我文文静静的母亲。她以为她还像以前那样,在诱惑的大棒下坚强不屈。
“拿儿子开这种玩笑,你恶不恶心?”那晚夫妻俩正火热,刘璐的底线都永远鲜明,“你怎么敢拿你亲儿子开涮?”
但我想这都过去了。
今晚的计划,本来是去药高一的英语老师,但李晓修看过他同学妈妈的脚,心生歹念。计划有变,我和李猛现在回家,还没有事先和张亮平说。
“当然更爱你……”
我们悄悄带上门,只听书房里,传出刘璐和张亮平的动静。
“一家之主,”她边说边喘,“行了吧?”刘璐把我带到大,我还从没听过她哄过男人。
没有前文,但我晓得她在回答啥问题。书房里传出湿腻的水声,像是舌头和舌头在你来我往。
儿子不在的时候,家里就没有冰山小姐了。那只有一只被驯服的老母猫。爸爸操妈妈,正常又不正常,无论问她多下贱的问题,她都乖乖回答。
我不在的时候,连书房都性欲翻腾,不会再有什么寡淡的小妇人,盘着腿,端坐在高脚凳上,守候儿子回家。
冰山小姐还盘着腿,但是不坐了,而是仰卧在高脚凳上。
她两只交叉的脚踝,被张亮平一手抓住,成了炮架子。
她头顶的髻被揪着,男人挺着腰,阳具在她仰起的盆腔中,进进出出。
张亮平偷看了一眼门外,而刘璐深情地看着丈夫,不晓得自己儿子正站在身后,目睹她的痴态。
他取出一管蓝水,让她冷白的脸颊,泛起古怪红温。
这是她想要的,但她晓不晓得游戏背后的规则?
在她清醒的时候,丈夫和李猛是不会同时出现的。
除非不清醒。
“你还闹离婚吗?”张亮平大声问,故意说给人听。
三个月前,他苦苦哀求她,但刘璐笑得无奈,又那么笃定,儿子在场,无法忘怀,因为她扬起下巴,绝不低头,“我只要离婚。”
“还问?”一样是这小妇人,正舔他的乳头,像狗一样,“问上瘾了你?”
“老实说!”张亮平捏紧了刘璐的头,用力插她。
“不离婚……!”她松开嘴,气息乱了。
“真的?”
“真的,我不离……!”被驯服的呻吟,“不离婚了……不离婚了!”
一双大白腿依旧盘着,交叉的双脚上下摇摆,高脚凳不停晃动,地板蹭得嘎嘎响,热液爬下凳子腿,流得满地都是。
我早先在学校里泄过的火,又燃起来,我由它燃着,因为一会儿还能再泄。
书房的窗上溅上一片水珠。起热雾了,但没有人再画一个笑脸。
生活会一直这样过下去。她快乐,我快乐,他也快乐。
为了得到什么固定的东西,我们都被什么所教化,有的是规矩,有的是另类的规矩。
有人有分寸,有人忘了分寸,还有人被剥掉了分寸。
刘璐吸吮着涂抹快感的鱼钩,我不会取笑她,而是在央求鱼竿的道上拜叩。
我们都是被驯服的狗,盼着第二天的骨头,谁也别笑话谁。
——完——

![[红楼]侧妃被迫努力+番外](/img/4590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