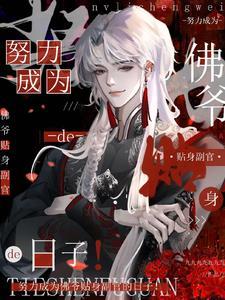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学霸的军工科研系统 > 第226节(第1页)
第226节(第1页)
“不如我们去旁边边吃边聊?”
常浩南低头看了一眼盘子里的肉饼提议道。
……
几分钟后,两个人坐在了旁边一处不太起眼的长桌边上。
“这个项目主要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在41o厂之前那台电火花打孔设备的基础上升级,开一种微细电火花加工数控机床,二是针对高铌钛铝合金材料开新的熔模精密铸造工艺。”
“前面做电火花加工那部分,我们目前完成的比较顺利,已经进入了样机研制阶段,但是后一项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熔模铸造过程同时涉及到力、热、电的作用,并且材料的性能和晶相情况本来就受到元素成分的影响,自变量实在太多,我们几乎用尽了目前能想到的手段,还是没办法很好地模拟出整个连续,或者哪怕是半连续铸造过程。”
魏永明介绍完情况,常浩南马上就明白了41o厂这是要干什么。
由于涡喷14计划的顺利完成,他们这是在升级设备,准备进行第三代涡扇动机的生产!
电火花加工系统自不必说,三代大推的涡轮前温度会提高到12ooc的水平,需要更加复杂的主动冷却技术,除了在设计上更加困难之外,对于加工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而第二项里面提到的高铌钛铝合金,则由于其高熔点、高强度、高模量和低密度的优势,成为先进航必不可少的材料之一。
换句话说,在经过了十年的反复之后,涡扇1o,终于迈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步。
这是41o厂的一小步,却是华夏航空动力产业的一大步。
还是中午或者下午
如题,最近学校里的事比较多,回到两更状态(要是我也有个能帮我写论文的系统就好了)
第297章多物理场仿真
想到这里,常浩南突然觉得魏永明这个名字似乎有点耳熟。
他十分确定这是自己重生以来第一次和青华大学产生接触。
那么就应该是前世听过的人。
“铸造工艺试验需要大量财力和时间,而您也知道,这两样正是我们现在最缺少的,目前美日俄这些先国家已经对钛铝合金有了很多年的研究,我们靠传统手段很难在短时间内追上他们,但是目前我们所用的解耦合手段基本已经走到了死胡同里,项目组在后续的路线选择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在简单介绍了目前的情况以及面临的困难之后,魏永明带着期望的眼神向常浩南问道:
“所以,我这次来是想向您请教一下,以目前的技术手段而言,是否有可能像流体力学或者结构力学一样,通过数值计算的方式,在计算机上面完成对铸造过程的仿真模拟?”
尽管只是个硕士生,但他的总结思路清晰条理分明,绝对是深度参与了整个项目,而非一个简单打下手的人。
他的这个问题,一时间甚至难住了常浩南。
实际上,这并不是后者第一次面对类似的问题了。
从之前在三座门的庆功会上,阎忠诚就提到过,黎明厂计划用1net马氏体不锈钢通过热锻方式生产航改燃气轮机的叶片,但材料的变形、传热和组织演化之间相互作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有限单元法在需要充分考虑微观组织影响的热锻造工艺中的应用。
而前段时间在关于海之星雷达的讨论中,郭林也曾经提到过,14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舰载大口径有源相控阵天线在太阳照射、风荷、盐雾侵蚀等环境载荷影响下,天线阵面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结构变形,恶化天线辐射性能,需要消耗更大的功率才能实现相同的射功率。
但是增加输入功率又会带来更大的热功耗,除了浪费军舰上本就宝贵的电能之外,对温度敏感的tr组件和阵面电源也会因此而产生性能温漂,导致tr组件输出的激励电流改变,进一步恶化天线的辐射性能。
这些问题虽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涉及到的领域也完全不同,但大家面临的困境都是一样的——
相比于基本只需要考虑力学影响的飞机气动和结构设计,它们设计到的物理场更多,并且相互之间还有非常紧密的影响,对于目前所流行的计算分析手段而言,没办法同时对这么多个物理量进行计算和寻优。
传统计算手段中,当引入非线性条件时,计算需要在多个偏微分方程组之间反复迭代多次以求获得收敛,但铸造问题同时涉及材料非线性、几何非线性和边界非线性,迭代效率极低导致计算时间需要以月甚至年为单位不说,最后的结果还有很大概率是散的。
而如果把这些物理场拆开来分别进行计算,又忽视了其中的耦合作用,导致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完全无法拟合。
就现有的技术手段而言,这个问题无解。
因此常浩南这段时间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编写一个新的、综合的多物理场仿真建模软件。
但这需要很高的、至少过目前这个时代的理论支持。
也是他迫切地想要把系统的理论能力等级升到1v3的原因。
在花了些时间总结语言之后,常浩南以谨慎乐观的方式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传统的解耦合手段,包括才展出来不久的间接耦合手段都只能处理多物理场之间的弱耦合问题,强耦合问题不可能被直接解耦,所以继续在这个方向上进行尝试的意义确实不大。”
“比如你刚刚提到过的铸造过程,会涉及到一个流固耦合,只有在微小形变量假设下,这才是个弱耦合问题,因为流道会对流体产生影响,但反过来流体对流道的作用就可以被忽略,这样的问题可以解耦解决。”
“但铸造过程并不符合这个假设……”
魏永明的眼神稍稍黯淡了下来,显然,他是希望能够继续通过数值计算方式走下去的。
因为这是华夏唯一有可能实现技术跨越的途径。
“是的,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常浩南点了点头:
“我正在开一种全耦合求解法,如果顺利的话,那么……”
多物理场仿真如果归纳成数学问题,其实就是求解非线性程度极高的偏微分方程组,但由于工程上只需要数值解并不需要解析解,因此总体难度应该还好。
另外在原来的时间线上,fem1ab也是在2oo5年改名为comso1mu1tiphysics并正式涉足多物理场仿真领域,在时间跨度上也就是8-1o年的水平,1v3级别的理论应该足以应付。
更何况工程软件这种东西,总归是需要收集数据做版本迭代的,不可能指望着就是尽善尽美,而哪怕现阶段只能把最基本的力热耦合做出来,对于几乎所有的行业来说,都堪称一个巨大的助力了。
“如果顺利的话,那么下半年有可能出一些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