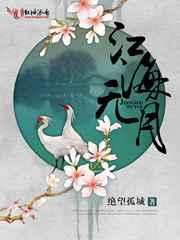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学霸的军工科研系统 > 第1065节(第2页)
第1065节(第2页)
所以在任何真正的研究项目之前,他先需要一个辅助设备。
高音风洞!
而这,可以说是常浩南最熟悉的领域了。
没有之一!
要知道,在重生之前,他就是jf22风洞的相关技术人员。
虽然那时只是个并未参与到核心设计当中的普通工程师。
但对于高音风洞的总体情况和技术难点,却是再熟悉不过……
“高声飞行器周围出现了空气热化学反应,表现出非线性、多物理和多尺度的特点……
当温度在2oook左右时,氧气分子弛豫时间大约是千分之一秒,而6oook时,则大约是o。1微秒,按照飞行度6oooms计算,那么达到第一个弛豫时间的平衡长度为6米,,也就是说对于6m长的飞行器,头部激波后具有不同的激波温度,飞行器周边的气体总有一定区域的气体处于非平衡状态……”
为了表达自己的重视程度,他没有使用电脑和打印机,而是在一页纸上奋笔疾书:
“可靠的高声地面试验必须满足三个关键需求,一是复现给定高声飞行条件下的气流总温,例如在高度3okm、马赫数为7的飞行条件下,风洞试验气体的总温应该为27ook,此时飞行器模型驻点区的氧气已经开始解离。对于马赫数为1o的飞行,气流总温过了45ook,氮气分子开始解离……
因此,现有的任何风洞都不足以支持马赫数为6以上的高音研究,应当考虑在涪城基地新建一座采用爆轰驱动技术的新型风洞,以支持我国大气层内高音飞行器的研制工作!”
第1172章五种构型
常浩南的这份报告看似有些突兀,但其实卡住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间点。
实际上,华夏在高音方面的研究起步很早。
在5o年代中期,华夏连第一枚导弹都还没成功射的时候,钱学森和郭永怀两位前辈就在中国科学院机械所组建了一个“激波风洞”研究小组,开始从战略层面规划高音的技术研究。
要知道那个时候,哪怕是美苏两极,也尚未从工程层面确定下来具体用何种技术手段才能实现高音飞行。
但相关部门和领导还是意识到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挤出部分资源,支持建造了jf4直通型、jf4a反射型激波风洞。
并最终于1969年一鸣惊人,搞出了代表当时国际顶尖水平的jf8冷高声风洞。
工作范围最高可达15马赫。
不过,传统空气动力学研究一般以“流动状态模拟”为准则,也就是根据缩小的飞行器模型,要求实验气流满足一些流动相参数,如马赫数和雷诺数相似。
而高声研究,更加关注的是“飞行条件复现”,要求实验气流的度、静温、静压、介质成分、特征尺度等主要参数与实际飞行条件相同。
例如在马赫数为7的飞行条件下,传统风洞即便能够模拟出这一度的气流,但实验条件下的气体总温也只有648k,远不及实际飞行条件下的25oo-3oook,根本无法复现高声流动的核心物理现象。
因此,jf8这样的风洞仍然存在很大局限。
要想真正进行切实可用的高声研究,还需要在保证气流度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风洞工作总温。
针对这一目的,欧洲、日本和美国分别相对独立地展出了自由活塞驱动和加热轻气体驱动两条技术路线。
然而这两种方案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片面强调工作总温,但要想扩大实验流场和延长实验时间,则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代价。
对于上世纪的华夏来说完全无法接受。
好在,国内学者找到了爆轰驱动这一看似可行性很低的方案,并在863计划的支持下,通过1998年建成的jf1o风洞成功进行了初步技术论证。
而2oo5年这会,正好是高风洞路线选择的下一个关键节点。
因此,尽管报告递交上去之后并没有马上得到反馈,但常浩南倒是并不着急。
而是很快把精力放在了解决高维net-jouguet燃烧方程的理论层面……
……
果然,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时间,常浩南便接到了一通来自李忠毅的电话。
“李主任,你好。”
对方这通来电的目的,他可以说是心里门清,因此就连语气都是一副成竹在胸的架势。
但事实证明,常浩南还是有些低估了自己一份亲笔报告在上面产生的影响力……
电话那头的李忠毅甚至来不及寒暄:
“常院士,上级领导想在下周一邀请你去京西宾馆做个报告,让我询问一下你的安排是否方便?”
一句话,差点给常浩南直接干停电了——
像什么邀请、询问之类的用词,显然属于客气。
李忠毅的上级,开什么玩笑。
难道还能说不方便?
所以关键并不在这里,而是……
“报告?”
“在京西宾馆?”
常浩南一时间有点难以把这两个名词结合到一块。
京西宾馆在实际操作中隶属于总参管理保障部,级别和大会堂几乎在同一水平,而且隐秘性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