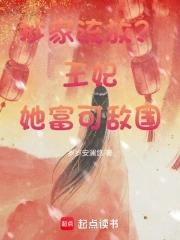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综影视:白浅被挖眼前觉醒记忆了 > 第10章 程少商重生了10(第1页)
第10章 程少商重生了10(第1页)
马车驶离灞水,程少商靠在车壁上,闭目养神。连日的劳顿让她的筋骨出细微的酸疼,但精神却异常清明。
回到都城,还未入程府,宫里的赏赐便已先一步到达。金银绢帛之外,文帝特意下旨,褒奖她临危受命、力保堤坝之功,特赐其“同中书门下议事”之权,虽非常设官职,却意味着她可参与某些重要朝会,就工器、水利等事宜表意见。
这道旨意,比之前的官职和金牌更引人侧目。
程府门前,程始领着全府下人跪迎,脸上是掩不住的激动与惶恐。萧元漪依旧没有出现。
程少商下了马车,目光平静地扫过众人。“起来吧。”她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仪。
她径直走向自己的院落,官袍未换,便先摊开了纸笔。灞水之险给她敲响了警钟,水利工程关系国计民生,必须系统整理,形成规制。
几日后的大朝会,程少商第一次以“同中书门下议事”的身份踏入宣明殿。
她站在文官队列的末尾,身形纤细,却站得笔直。周遭投来的目光复杂各异,有好奇,有审视,也有不加掩饰的轻蔑。
今日议题涉及来年漕运修缮。工曹呈上方案,依旧是老调重弹,增派民夫,加固堤岸。
一位老臣出列,侃侃而谈,引经据典,无非是“祖宗成法不可轻变”云云。
文帝听着,眉头微蹙,未置可否。目光扫过殿内,落在程少商身上:“宣宜乡君,你于水利既有心得,对此有何看法?”
霎时间,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
程少商出列,行礼,声音清晰沉稳:“陛下,工曹方案,稳妥有余,进取不足。”她开门见山,毫不避讳。“漕运之弊,不在堤不高,坝不固,而在泥沙淤积,河道迁改。只知加高堤岸,犹如筑墙阻水,终非长久之计。”
那老臣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程少商不理,继续道:“臣女以为,当效仿前贤‘分水杀势’之法,于漕运关键节点,择地修建滚水坝、分水堰,引导水流,冲刷泥沙。同时,改进疏浚工具,提升清淤效率。此乃臣女根据灞水经验,草拟的《水利疏浚及堤坝养护新法十条》,请陛下御览。”
内侍接过她手中的奏疏,呈给文帝。
文帝翻开,只见里面图文并茂,不仅阐述了原理,更列出了具体施工方法、物料配比,甚至还有新式清淤船和测量仪器的草图。条理清晰,数据详实,绝非空谈。
殿内一片寂静。许多官员面露惊异。他们没想到,这小女子竟真能拿出如此系统、可行的方案。
凌不疑站在武将班列中,看着殿中那个从容不迫的身影,目光深沉。她似乎总能在他以为已经看清她时,又展现出新的、令人惊讶的一面。
文帝越看越是欣喜,合上奏疏,朗声道:“好!详实具体,切中要害!便依程卿所奏,由工曹与你共同斟酌,择其善者,先行试点!”
“臣女领旨。”程少商平静谢恩。
退朝时,不少官员围拢过来,或真心请教,或试探结交。程少商一一应付,态度不冷不热,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
凌不疑走过她身边,脚步未停,只留下一句:“程丞今日,风头无两。”
程少商仿若未闻,径直走向宫外等候的马车。
程少商的《新法十条》很快在部分漕运河段试行。
效果立竿见影。清淤效率提升,河道通畅,漕运损耗明显降低。消息传回,朝中反对之声渐息。
程少商却并未停步。她将在灞水抢险时改良的糯米灰浆配方进一步完善,又结合将作监的工艺,研制出更坚固耐用的“三合土”,开始小范围用于官道修缮和城墙补葺。
她的庄子也成了“试验田”。新式农具、耐旱作物、甚至她根据记忆摸索出的堆肥之法,都在这里先行先试。庄子的产出和收益稳步增长,她手中的资本愈雄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