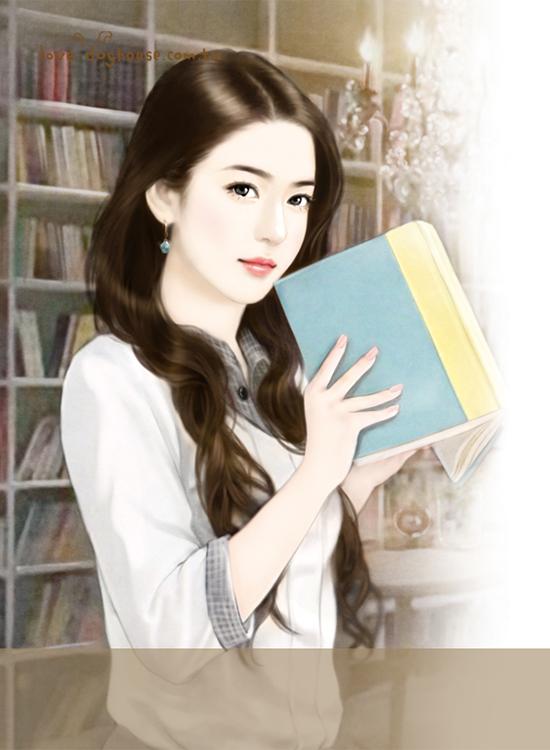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综影视:白浅被挖眼前觉醒记忆了 > 第13章 程少商重生了13(第1页)
第13章 程少商重生了13(第1页)
雪后的都城,空气清冽。程少商晋为将作监少监、赐紫金鱼袋的消息,比寒风传得更快,更刺骨。
程府内,下人噤若寒蝉,行走间都带着小心。程始欢喜之余,更多是无所适从,面对这个官阶已逼近自己的女儿,他连寻常父女的关切都有些难以启齿。
主院里,萧元漪对着窗外枯坐良久,手中的暖炉早已冰凉。程姎安静地陪在一旁,看着伯母沉寂的侧脸,心中五味杂陈。她如今已定下亲事,对方是门当户对的文官之子,前程可见,规矩方圆。可看着程少商一步步走到如今高度,她那份按部就班得来的“稳妥”,竟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她……病可大好了?”萧元漪忽然开口,声音干涩。
程姎愣了一下,忙道:“听闻已能下床走动,只是还需静养。”
萧元漪“嗯”了一声,不再说话。病中那日鬼使神差地去探看,指尖触及女儿滚烫的额头,那瞬间的心悸与慌乱,此刻回想起来,依旧清晰。可等她醒来,自己却仓皇逃离。有些裂痕,似乎从一开始就已注定,如今更是鸿沟难越。
程少商并未静养多久。
将作监少监的职责远比丞官繁重。她病愈后第一件事,便是上书文帝,请求系统勘查全国主要河道、官道状况,制定长期的修葺养护章程,并建立相应的物料储备与应急机制。
文帝准奏,命她主理此事。
这意味着她的权责范围,从技术督造,扩展到了部分工程规划与资源调配。她变得更加忙碌,巡查各地,审核图册,调配匠人物料。紫金鱼袋在她腰间随着步履轻晃,代表的不仅是恩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这日,她巡查完一条黄河支流的堤防,返回都城已是黄昏。马车行至街市,却被拥堵的人流挡住去路。
“前方何事?”程少商问随行护卫。
护卫前去查看,很快回报:“少监,是凌将军凯旋,百姓围观。”
程少商掀开车帘一角,只见长街尽头,旌旗招展,黑甲卫簇拥着一人一骑缓缓行来。凌不疑端坐马上,玄甲染尘,面容冷峻,周身散着久经沙场的肃杀之气。百姓欢呼雀跃,将瓜果鲜花抛向军队。
他目光平视前方,并未看向她这边的马车。
程少商放下车帘,吩咐道:“绕路。”
马车悄无声息地驶入旁边小巷,将身后的喧嚣与荣光隔绝。
凌不疑此次大胜归来,受封赏赐无数,风头一时无两。
庆功宴上,文帝看着座下这位战功赫赫又俊美无俦的义子,心思不免又活络起来。只是还未等他开口,凌不疑便率先出列,以“军务未靖,匈奴未灭”为由,再次干脆地回绝了任何关于婚事的试探。
席间众人神色各异。有惋惜,有不解,也有如三皇子般,目光在凌不疑和坐在女眷席末、正与身旁工曹女官低声讨论图纸的程少商之间逡巡,露出玩味神色。
凌不疑对此视若无睹。他的目光偶尔掠过那道专注于技术问题的身影,很快便移开。她腰间那枚紫金鱼袋,在宫灯下泛着暗沉的光泽,无声地昭示着两人之间已然拉开的、难以逾越的距离。
程少商对这一切浑然不觉,也无心察觉。
她的全部心思,都扑在了即将开始的漕运大清淤工程上。这是她主持制定的新规次大规模应用,关乎来年数百万石粮草能否顺利北运。
工程启动当日,她亲临现场。河岸上人头攒动,新制的清淤船、改进的挖掘工具、按照新法调配的加固材料堆积如山。
程少商站在临时搭起的高台上,并未多言,只简洁下达了开工指令。她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
匠人和役夫们早已熟悉她的规矩,令行禁止,工程有条不紊地展开。
凌不疑奉旨巡视京畿防务,恰好路过此地。他勒马停在远处高坡,看着河道中忙碌的景象,看着高台上那个指挥若定的身影。
她穿着便于行动的简便官服,髻束得一丝不苟,正拿着图纸与几位大匠快交流。阳光照在她身上,那枚紫金鱼袋熠熠生辉,竟比他那身荣耀等身的铠甲,更显得夺目。
他看了许久,直到副将前来请示,才调转马头,沉默离去。
有些风景,注定只能远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