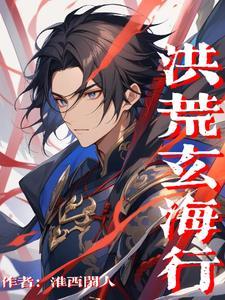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1946:系统绑定,家族传奇 > 第49章 哈默线--神探的棋局(第1页)
第49章 哈默线--神探的棋局(第1页)
o年初的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的空气里都浮动着资本躁动的气息。阿曼德·哈默站在他新购入的、俯瞰整个洛杉矶盆地的山顶庄园露台上,手中端着一杯加冰的威士忌,琥珀色的酒液在夕阳下折射出迷离的光。他脚下这片土地,连同中国山西即将破土的平朔露天煤矿、南海深处跃跃欲试的石油勘探船,都是他庞大商业帝国扩张的注脚。石松的预言,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正扩散向更广阔的领域。
他拿起卫星电话,拨通了那个直通香港太平山顶石氏庄园的加密号码。线路接通的度快得惊人。
“老哥!”石松那标志性的爽朗笑声传来,背景里似乎还隐约有轻柔的女声和杯盏碰撞的细微声响,“洛杉矶的阳光可还暖和?听说你又拿下了几个州的页岩气开采权?动作快过火箭!”
“比不上你,石。”哈默的声音带着由衷的叹服,“‘石氏芯片’…oo亿美金市值开盘,世界富的椅子,坐得还舒服吗?”他眼前仿佛浮现出报纸头版那耸动的标题和石松在纽交所敲钟时,身边两位新王妃惊世容颜带来的轰动。那个昏迷十二年、年才苏醒的男人,仅用三年时间,就用领先世界十年的“星辉一号”处理器、“幻影”显卡和独步天下的纳米光刻机,将硅谷巨头们踩在了脚下。哈默抿了一口酒,压下心中那丝懊悔——当初石松苏醒后寻求支持时(实际是福利),他只谨慎地投了o。现在看来,那简直是白捡的金山。
石松笑声更大,带着几分戏谑,“钱嘛,够用就行。中国那头‘睡狮’的生意,才是真正的大棋局。”
哈默失笑,“你可是把整个科技史都改写了。说到这个,”他话锋一转,语气真诚,“还要多谢你推荐的乔丹。我的人去看了,那个北卡的小子…石,你眼光太毒了。那是个…天生的征服者。他身上有种东西,让我想起年轻时的自己,但更纯粹,更…耀眼。”哈默的眼前闪过球探报告上那张扣篮的照片和乔丹阳光四射的笑容。
“哈哈哈!”石松听起来毫不意外,“等着看吧,这小子以后会让球鞋股票飞上天的!比你挖一百口油井都赚眼球!”
石松这种近乎全知的笃定,再次触动了哈默内心深处那根好奇的弦。一个近乎疯狂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他放下酒杯,身体微微前倾,仿佛要穿透卫星信号看清电话那头的人,声音压低了半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和玩笑:
“石,你好像…什么都知道?那…干脆告诉我,我阿曼德·哈默,还能活多久?”
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只有微弱的电流嘶嘶声。哈默甚至能想象石松此刻的表情——那双深邃的眼眸里,或许正掠过无数条交错的时间线。几秒钟后,石松的笑声再次响起,轻松依旧,却似乎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意味:
“老哥,放宽心!日子长着呢。”
哈默的心跳漏了一拍。石松没有给出具体数字,但那句“日子长着呢”和笃定的语气,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暗示和安抚。他深吸一口气,决定将试探推向极限:
“既然日子还长,再推荐一个…‘优秀’的。”他刻意模仿了石松当初推荐乔丹时的用词。
这一次,石松的沉默稍长。哈默几乎能听到听筒里传来的、手指轻轻敲击红木桌面的声音,那是石松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嗯…”石松的声音变得更为沉静,带着一种筛选信息的慎重,“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有个华人博士,叫李昌钰(henryg-yulee)。”
“李…昌钰?”哈默迅在脑海中搜索,这个名字并不像乔丹那样完全陌生,似乎在某个关于重大案件的新闻报道角落里出现过,但印象模糊。
“对,就是他。”石松的语调恢复了那种洞悉一切的淡然,“如果你能和他联手…”石松顿了顿,仿佛在掂量词句的分量,“…你们能改变的,将是某一种…科学展史。他会是你最锋利的‘手术刀’,切开那些挡在你帝国前面的迷雾和陷阱。”
“刑侦科学?手术刀?”哈默的商人思维飞转动。石油、煤矿、跨国贸易、复杂的政商关系、价值连城的艺术收藏…哪一个领域不需要一双能穿透谎言、还原真相的眼睛?石松的暗示如同闪电,瞬间照亮了无数潜在的应用场景——商业间谍、内部舞弊、安全事故、艺术品伪造、甚至是…人身威胁。
哈默的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沉稳,但眼底闪烁着锐利的光芒,“纽黑文大学,李昌钰博士。谢了,这份‘礼物’,分量十足。”
---
几周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冬末的寒气尚未完全褪去,灰蒙蒙的天空下,纽黑文大学一栋不起眼的旧实验楼显得格外冷清。穿着考究驼绒大衣的哈默,在几名低调的随行人员陪同下,踏入了弥漫着淡淡化学试剂气味和旧纸张味道的走廊。与洛克菲勒中心的奢华或钓鱼台国宾馆的庄重相比,这里朴素得近乎寒酸。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李昌钰的实验室门开着。哈默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伏案工作的身影——中等身材,穿着整洁但洗得有些白的实验服,头梳理得一丝不苟,侧脸线条透着东方人特有的温和与专注。他正全神贯注地通过一台老式双目光学显微镜观察着什么,对门口的访客毫无察觉。
“李博士?”哈默的助手轻声唤道。
李昌钰闻声抬起头。他的眼睛不大,却异常明亮有神,像探照灯般瞬间扫过门口的众人,精准地落在被簇拥在中间的哈默身上。他脸上没有太多惊讶,只有一种沉静的、职业性的审视。他站起身,动作利落,伸出手,声音平和而清晰:
“哈默博士?久仰。欢迎来到纽黑文。”没有多余的客套,目光直接而坦诚。
哈默握住他的手,感受到一种与不同的力量——这不是政治家的厚重,而是科学家特有的、基于知识和逻辑的稳定与自信。“李博士,打扰了。有人向我极力推荐您,说您是能‘看见真相’的人。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李昌钰微微一笑,那笑容含蓄而睿智,带着洞悉世事的了然:“过誉了。真相就在那里,只是需要耐心、方法和一点点运气去现它。”他侧身示意,“请进,地方简陋,见笑了。”
实验室确实不大,设备多是些看起来有些年头的分析仪器和显微镜,但每一样都擦拭得锃亮,摆放得井井有条。墙上挂着一些复杂的化学分子式图表和几幅放大的、令人费解的痕迹照片(指纹、弹痕、纤维)。一种严谨、专注、追求极致细节的氛围弥漫在空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