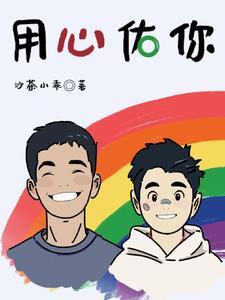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 第165章 老麦克风底下还压着半句话(第2页)
第165章 老麦克风底下还压着半句话(第2页)
尤其是一位拄拐的盲眼老教师,总在“被退学的儿子”那段播放时微微侧头,像是在辨认什么。
他的嘴唇偶尔会轻轻动一下,仿佛在无声地接话。
第章那些没说出口的,终将回响
夜风掠过西部小城的纪念展廊,石碑在月光下泛着冷白的光。
林晚裹紧风衣,第三次踱步经过碑林时,脚步终于停了下来。
她原本只是例行巡查,确认“补白计划”落地项目的数据同步正常。
可连续三晚,她都看见那几位老人——佝偻着背、拄着拐杖、眼神浑浊却执着——准时出现在这里。
他们不交谈,不靠近,像一群沉默的守望者,在声音响起时微微颤动肩头,在某一段结束时悄然转身离去。
最让她心头一震的,是那位盲眼老教师。
他每晚六点整出现,由邻居搀扶而来,坐在离“被退学的儿子”那段录音最近的长椅上。
当低频音频缓缓流淌而出,他总会侧耳倾听,嘴唇微动,像是在无声接话。
那一瞬,林晚几乎以为他要开口了。
直到今晚。
录音播放完毕,人群散去,林晚正准备上前检查设备运行状态,却见老人忽然抬起手,摸索着从怀里掏出一支老旧的盲文笔和一小块硬纸板。
他的手指缓慢而坚定地刻下凸点,动作极轻,仿佛怕惊扰了这片刚刚沉寂下来的空气。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林晚没有打扰,只是静静站在几步之外。
良久,老人停下动作,将纸片递向身旁的学生志愿者:“帮我……念一遍。”
少年接过,低头辨认后轻声读出:“我不怕死,我怕你们忘了为什么有人要说话。”
声音不大,却如一道闪电劈开寂静。
林晚怔住。
这句话没有情绪起伏,没有控诉或哀伤,却比任何呐喊更沉重。
它不是求救,而是警示;不是回忆,而是遗嘱。
她本可以立刻上传这段记录,纳入“补白计划”的官方归档。
但她没有。
她蹲下身,对少年说:“把这句话,一个字一个字誊抄下来,明天开始,每天在校广播里读一次。”
“为什么?”少年不解。
“因为有些话,不该只留在碑上。”林晚望着老人渐行渐远的背影,“它们得被人听见,再传下去。”
三天后,该县教育局正式推出“口述轮值制”试点——每周由一名学生、一位居民、一名退休职工登上社区讲台,讲述自己从未公开的故事。
期开场白,正是那句盲文写下的话。
而千里之外的北京,陆承安正站在《公共表达权司法解释》专家研讨会的言席前。
会场鸦雀无声。
这位以冷静着称的律政精英,罕见地没有引用判例或条文。
他只是轻轻按下播放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