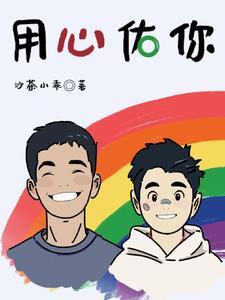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 第195章 雪化时名单浮出水面(第2页)
第195章 雪化时名单浮出水面(第2页)
而这家印刷厂,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注销。
更关键的是,它的法人代表姓周,与周晓虹是同乡!
所有的线索,如百川归海,再次指向了那个看不见的、系统性的掩盖网络。
与此同时,赵小芸的“蓝布衫行动”正借着互联网的东风,影响力日益扩大。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她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全国知名的《南方周末》上,开设了一个名为《我们没同意》的专栏。
第一期,就刊登了陈德海那本工作日志的摘录,以及一篇由他口述、赵小芸整理的匿名忏悔信。
文章的结尾,赵小芸写下了一段振聋聩的话:“不是所有加害者都戴着面具,有些人,用尽一生都在替别人擦拭手上的血。”
一石激起千层浪。
舆论场瞬间被引爆,迅分化成两极。
有人痛斥陈德海是鳄鱼的眼泪,是体制的帮凶,现在出来忏悔不过是虚伪的自我感动。
但更多的人,却在评论区留下了自己身边类似的故事——“我们镇上当年的那个民政干事,后来也信了佛”、“我爸就是派出所的,他说那几年总做噩梦”。
赵小芸趁热打铁,立刻起了“沉默见证人计划”,设立了一个高强度的加密邮箱,鼓励那些深藏在体制内、同样被良知拷问的知情者,以匿名的方式,提交他们所知道的碎片化证词。
一时间,无数封来自全国各地的加密邮件,如雪片般飞向了这个小小的端口。
另一边,陆承安从“印刷厂”这条线索中,嗅到了更深层次的犯罪气息——这可能不仅仅是掩盖真相,更涉及到伪造公文罪和巨额国有资产流失。
他以公益诉讼的名义,向省档案局正式申请调取“红星印刷厂”的工商原始档案。
然而,回复冰冷而强硬,只有两个字:涉密。
这块“国家机密”的挡箭牌,坚不可摧。
但陆承安并未就此罢休,他指导赵小芸团队,转换策略,联系上了当年印刷厂的一批原职工子女,以“老工业区口述史征集”为名,组织了一场看似温情的访谈活动。
在一个退休工人的儿子家中,一段不经意的回忆,成了刺破铁幕的利刃。
“我爸当年是厂里的排字工,他总说,咱们厂半夜偷偷来印的东西,最怕见光。那玩意儿邪性,一张张表格,抬头都印好了,就是内容全是空格,专门等着往里填名字的……”
这段录音,被悄悄保存了下来,成为了对抗那块“涉密”挡箭牌最关键的佐证。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黎明将至时,一则紧急线报如寒流般涌入苏霓的指挥中心。
“报告!桦林镇传来消息,陈德海家昨夜遭到不明人士恶意断电,院墙外现了几个陌生的、踩踏过的脚印!”
苏霓的心猛地一沉。
对方动手了!
他们已经察觉到了陈德海这个薄弱环节,准备用物理手段让他永远闭嘴。
“林晚,立刻暂停与陈德海的一切深入接触,转为外围保护!”苏霓的指令不容置疑,“许文澜,把陈德海日志的核心数据全部脱敏处理,去除个人信息后,立刻上传至国际学术共享平台,打上‘二十世纪末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资料’的标签,让它成为全世界学者都能看到的东西!”
这是警告,也是一道护身符。
一旦资料公开,任何人再想对陈德海下手,都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审视。
做完这一切,苏霓静静地看着窗外。夜色渐浓。
而此刻的桦林镇,风雪已停。
陈德海独自一人,走进了那间空无一人的培训教室。
他没有开灯,只是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走到黑板前,拿起一截粉笔。
黑暗中,响起“沙沙”的写字声。
他写下了一行字:“粮站东仓,第三排地砖下,埋着当年的移交清单。”
写完,他放下粉笔,走到自己白天坐过的那个位置上,静静地坐下。
他没有恐惧,也没有不安,表情平静得像一潭深水,仿佛只是在等待一个约好的人进来。
窗外,屋檐上积压的残雪开始融化,一滴,一滴,有节奏地落在下方的石阶上。
滴答,滴答。
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像一枚正在倒计时的秒针,也像有人在不远处,正一步步走来。
喜欢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请大家收藏:dududu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