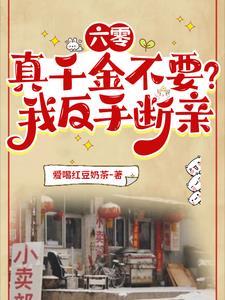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 第198章 蓝布衫在说话(第2页)
第198章 蓝布衫在说话(第2页)
“让我看看他病得有多重。”
数据流无声地诉说着真相。
李老师的手机信号自进入医院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特定病房的范围,其数据流量更是低得如同关机。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这不是治疗,这是软禁!
对方的反应度乎想象,他们正在剪除一切可能暴露的线索。
“不能再等了。”陆承安的声音沉稳如山。
他没有选择报警,那只会陷入无休止的扯皮和调查。
他以基金会法律顾问的身份,直接向省教育厅出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函。
函件内容直指那所重点中学,举报其“存在违规使用敏感历史材料作为教学资源”的现象,并援引相关法规,申请介入调查。
这一招,是釜底抽薪。
它将皮球狠狠地踢给了地方当局。
如果他们拒绝配合调查,就等于坐实了“掩盖事实”的嫌疑,事件性质将立刻从一所学校的内部问题,上升为整个教育系统的丑闻。
压力,瞬间转移。
阳谋,无懈可击。
果然,第二天上午,那位“病重”的教研组长便奇迹般地“康复”出院,并主动联系了基金会。
在学校一间空旷的会议室里,这位头花白、眼神中带着一丝惊惧和决然的老人,从一本磨破了角的语文课本夹层中,抽出一个牛皮纸包裹的笔记本,郑重地交到了苏霓手上。
笔记本的封面上,是一行用钢笔写下的,力透纸背的字:
“他们删正文,我们就抄边角;他们烧纸,我们就刻墙。”
当晚,基金会核心成员的闭门会议上,气氛凝重如铁。
苏霓翻开那本泛黄的笔记本,指着其中一页绘制得如同蛛网般复杂的“基层权力传导链条图”,声音清冷而坚定:“我们的对手,已经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清洗。他们要抹去的,不仅仅是档案,更是承载记忆的物理实体。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完成之前,启动三级响应。”
她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
“第一级:技术固证。文澜,将周素琴笔记全部高精度扫描,把这些数据拆分成无数碎片,嵌入我们即将布的社区治理app最新更新包里。只要有一个用户更新,我们的证据就多一个分布式备份。他们永远也删不干净。”
“第二级:记忆唤醒。小芸,立刻牵头组织‘口述史抢救工作坊’,动员所有能找到的、与那段历史相关的亲历者,录制音频。不用说得太明白,让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讲那些‘被消失’的亲人、朋友。所有音频故事,标题统一为——《我记得你没死》。”
“第三级:规则反制。承安,根据这份笔记里的流程和这份权力图,起草一份《关于建立重大公共记忆保护机制的立法建议》,我们要把它送进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题研讨会。他们用规则抹杀记忆,我们就用更高级的规则,把记忆焊进国家的法律里。”
三道指令,层层递进,从技术、人心到制度,构建起一张天罗地网。
深夜,喧嚣散尽。
苏霓独自一人回到了空无一人的纪念馆。
她站在那件蓝布衫的展柜前,静立了许久。
月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洒在玻璃柜上,反射出清冷的光。
这一次,她的目光没有停留在衣襟,而是落在了衣领处。
那里,有一道极其细微的折痕,以一个非同寻常的角度向内折叠,像一个凝固了数十年的手势印记。
苏霓戴上白色手套,在获得特别许可后,打开了展柜。
她的指尖轻柔地抚过那粗糙的蓝布,当触及那个折痕时,一个微小的、几乎无法察觉的硬结,硌了她的指腹一下。
就是这里。
她小心翼翼地拆开那处的缝线,一枚被蜡封住的微型胶卷,从布料的夹层中滑落出来,躺在她的掌心,冰凉而沉重。
许文澜连夜冲洗。
当图像在暗房的药水中缓缓显现时,在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那是一张八十年代某个会议室的偷拍照。
画面昏暗,但桌上摊开的一份文件标题却异常清晰——《关于在部分地区试点推行“死亡替代方案”的可行性报告》。
而在文件的参会人员签到名单末尾,一个龙飞凤舞的签名,让苏霓的目光彻底凝固。
那是现任基金会副秘书长,周启明年轻时的笔迹。
苏霓凝视着照片上那个意气风的青年,许久,缓缓将这张唯一的、能够一击致命的原件锁进了保险柜,只留下一句轻得几乎听不见的话。
“明天,让孩子们来做题。”
夜色深沉,纪念馆外,那棵百年银杏树上系着的蓝丝带,在晚风中轻轻晃动,像一个无声的回答。
一场看不见的考试,即将在黎明时分,拉开序幕。
喜欢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请大家收藏:dududu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