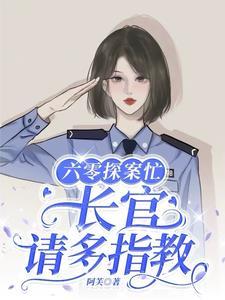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 第203章 活人写的史(第1页)
第203章 活人写的史(第1页)
那刺骨的寒意,顺着陆承安的脊椎一路攀升,仿佛焚化炉的烈焰并非烧灼纸张,而是直接炙烤着他的灵魂。
黑暗的深渊已然洞开,他要做的,就是把所有人都从那边缘拉回来,哪怕是与深渊本身为敌。
他几乎没有片刻迟疑,指尖在键盘上化作了风暴。
一份名为《关于立即叫停东仓系统非法档案处置行为的紧急法律意见书》的文档,在他的敲击下迅成型。
这不仅仅是一封法律文书,更是一柄出鞘的利剑。
“即便程序合法性存疑,也不能成为毁灭证据的理由!”这句被加粗的标题,如同一记重锤,敲在每一个可能看到这份文件的人心上。
陆承安的真正杀招,在于他创造性地援引了《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帮助毁灭证据罪”的共犯理论。
他用冰冷而精准的法律语言,剖析了焚烧行为的本质,明确指出,任何参与其中的公务人员,无论层级高低,只要执行了焚烧指令,就构成了这一罪名的共犯。
他们将不再是隐藏在庞大系统下的无名齿轮,而是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个人法律责任的独立个体!
这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威慑。
它绕过了对体系的直接控诉,转而将矛头精准地对准了每一个具体的执行者。
文件定稿,陆承安做了两手准备。
一份,通过全国人大常设的信访系统,以加密通道直递最高层;另一份,则在同一时间,公开布于“灯塔”基金会的官方网站。
前者是向权力中枢的正式宣战,后者则是引爆公众舆论的雷管。
效果立竿见影。
短短两个小时,基金会官网的服务器几乎被挤爆,该文书的阅读量以一种恐怖的度突破了百万大关。
网络上,一股由法律界人士率先带起的讨论风暴,正迅席卷全网。
几乎在陆承安按下“送”键的同时,苏霓的指令也已下达。
她将这个行动命名为——“我活着,我作证”。
赵小芸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拨出,目标正是此前那场被强行中断的直播中,最后言的那五位亲历者。
苏霓的计划清晰而大胆:邀请他们,携带所有能证明自己身份和遭遇的原始材料,秘密赴京,参加一场闭门听证会。
“常规的出行方式太容易被拦截。”苏霓的语气冷静得像一位战地指挥官,“我们必须把他们的行程全部拆散。”
一场精心策划的“隐形迁徙”开始了。
去北京的理由被伪装得天衣无缝:“带孙子去都看升旗”、“去探望远房亲戚”、“参加一个老年大学的书法交流会”……他们乘坐不同班次的火车、长途汽车,甚至自驾。
住宿被巧妙地安排在了几所不同高校的内部招待所,这些地方人员流动杂乱,且极少纳入警方的重点监控网络。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许文澜彻夜未眠,开出一个临时的加密通讯群组。
她给这个群组起了一个诗意的代号:“银杏叶”。
每一位赴京者和沿途接应的志愿者都在群内,一旦有人过预定时间未报平安,系统将立刻触最高级别的预警。
这条看不见的通讯线路,是他们生命安全的最后保障。
听证会当天,北京一家高校招待所的简陋会议室里,气氛肃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