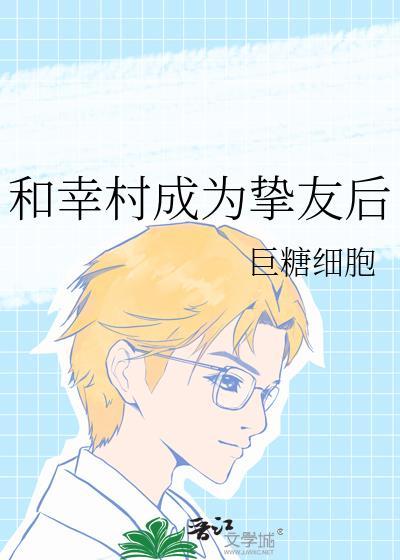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 第212章 课本里长出树(第1页)
第212章 课本里长出树(第1页)
教育部派来的工作组气氛严肃,为的中年男人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刀,仿佛能直接剖开人心。
他们坐在苏霓对面,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微弱的送风声。
这阵仗,不像是来调研,倒更像是来问罪。
苏霓没有丝毫的紧张。
她甚至没有碰一下桌上那份早已准备好的、关于“空骨灰盒”案件的始末陈情。
她只是平静地打开投影仪,屏幕上亮起的不是文字,而是一组冰冷又灼热的数据。
“各位领导,在讨论具体的争议之前,我想请大家看一样东西。”她的声音清澈而稳定,瞬间攫住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这是我们纪念馆的‘记忆角’项目在过去三个月里,收集到的部分数据。”
屏幕上,一个巨大的数字跳了出来:,。
“一万两千八百四十七条来自全国各地的口述历史记录。”苏霓的指尖在笔记本电脑上轻轻一点,数据图表生了变化,一个高达百分之九十一的扇形区被标成了刺目的红色。
“其中,百分之九十一的记录,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因基层治理失范、历史问题处理不当,对家庭几代人之间造成的信任撕裂与情感创伤。”
她没有提那篇论文,更没有提那场官司。
她只是像一个最客观的研究员,将一个个匿名的、浓缩了悲欢离合的故事,化为冷峻的数据,呈现在这群决定着未来的政策制定者面前。
“一个孩子的爷爷,因为当年的某个身份认定,一辈子抬不起头,直到去世,家人还在为一张证明奔波。这个孩子问我们,为什么课本里的英雄那么光辉,他的爷爷却像个活着的罪人。”
“一位母亲,因为娘家在特殊时期的土地问题,几十年不敢回乡,她的女儿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外婆葬在哪里。女儿问我们,是不是有些历史,注定只能成为秘密。”
苏霓关掉投影,会议室重归寂静。
她环视着陷入沉思的工作组成员,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所以,各位领导,孩子们不是不相信历史,他们只是不相信那些言辞闪烁、不敢直面伤痛的大人。”
长久的沉默之后,工作组组长深吸一口气,他没有再提“争议问题”四个字,只是对助手说:“把苏馆长提供的所有资料,全部拷贝一份,我们带回去。”
就在工作组返京的同一天,陆承安的雷霆一击也精准地送达了教育部的最高决策层。
一份名为《关于在思想政治课程中增设“公共记忆与公民权利”专题的建议案》的报告,被他通过特殊渠道,直接递交到了课程改革委员会的核心成员手中。
这份建议案,远非一份空泛的学术报告。
它的附录,才是真正的杀招。
附录一,是周茂才亲笔写下的那份“心里账”,字字泣血,记录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身份标签,而被剥夺了尊严、家庭和最终的安息之地。
附录二,是“空骨灰盒”主题展览上,数千名观众的留言摘录。
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写满了普通人相似的迷茫与痛苦——“我家的事,和这个一模一样”、“原来不止我们一家这样”。
附录三,更是釜底抽薪的一击——来自三千名中学生的匿名问卷调查摘录。
一个个尖锐的问题,直指现有历史教育的苍白与空洞:“如果历史都是完美的,那我们还需要奋斗什么?”、“为什么我们只学习成功,却不学习如何面对失败和错误?”
在报告的结语中,陆承安用加粗的黑体字写道:“我们的下一代,需要的不是被无菌环境层层包裹的纯洁叙事,而是直面人性与社会复杂性的勇气和智慧。教会他们理解这一点,是教育者最根本的责任。”
两周后,消息传来,这份石破天惊的建议案,被正式纳入了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研讨议程。
与此同时,一场无声的渗透,正在许文澜的操盘下悄然展开。
她秘密联络了多位参与教材编写,但身处外围、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学科专家。
她没有直接塞给他们观点,而是提供了一份精心制作的“隐形植入包”。
包里没有任何敏感词汇,全都是以“教学案例”形式出现的真实事件改编。
比如,一篇题为《村庄的变迁:集体迁坟引的土地权属再思考》的案例,深度剖析了某村因历史遗留的坟地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爆的激烈矛盾。
又比如,一篇《“不存在”的父亲:身份异常对子女社会权利的影响探究》,讲述了一个父亲的档案身份缺失,如何让他的孩子在升学、就业中处处碰壁。
所有案例都隐去了具体的地名、人名和精确的时序,只保留了最具普遍性的结构性矛盾。
这些材料以“最新学术参考与田野调查资料”的名义,像细雨一样,润物无声地流入了教材编写的各个分组会议。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专家们在讨论章节逻辑时,会不自觉地引用这些“鲜活”的案例,来支撑“社会展中的问题与挑战”这一章节的骨架。
如果说陆承安和许文澜走的是上层路线,那么赵小芸则将战火烧向了最广袤的基层。
她策划了一场名为“课本漂流计划”的行动。
她将“记忆角”中那些最具代表性的口述故事精选出来,重新排版,印制成一本本仿照教科书样式的小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