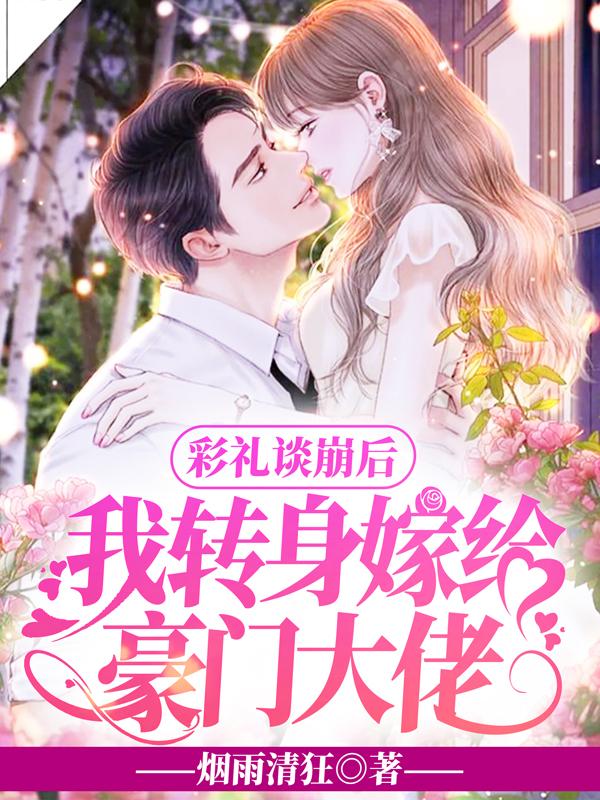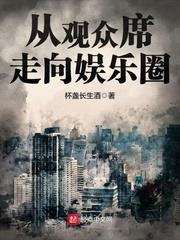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 第271章 这无声的证据比任何辩解都更加雄辩(第1页)
第271章 这无声的证据比任何辩解都更加雄辩(第1页)
话音未落,陆承安的手机与赵小芸的手机同时出尖锐的震动。
一条来自他们团队内部紧急频道的短讯,像一根烧红的钢针,刺破了空气中短暂的宁静。
“银杏记忆角,被拆了。”
赵小芸的瞳孔骤然收缩,她几乎是立刻就冲出了报刊亭。
冰冷的夜风灌进她的衣领,却丝毫无法冷却她胸腔内升腾的怒火。
陆承安的警告言犹在耳,而那股看不见的力量,已经用最粗暴直接的方式,宣告了它的存在。
半小时后,赵小芸站在空空如也的社区宣传墙前,指尖抚过墙面上被强行撬开展板后留下的狰狞划痕。
几个小时前,这里还挂着老人们的笑脸和他们亲口讲述的往事录音。
而现在,只剩下一张a纸打印的官方通告,字迹冰冷如铁:“因部分展示内容引群众情绪不稳定,存在不可控因素,经研究决定,‘银杏记忆角’即日起暂停展出,进行整改。”
社区居委会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那位姓李的主任正不耐烦地喝着浓茶。
面对赵小芸的质问,他把茶杯重重一顿,指着墙角一个不起眼的收缴箱。
箱子里,被撕裂的展板碎片像一堆垃圾,其中一段录音的文字稿恰好露了出来:“我没抢,可也没轮上。”那是一位退休老教师在讲述当年单位分房时的无奈。
“就因为这个?”赵小芸的声音因极力压抑而微微颤。
“赵同志,你要理解我们的难处。”李主任换上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哪怕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也不能随便播。过去的事,提多了,人心就乱了。我们这是为了维护社区的和谐稳定。”
赵小芸死死盯着他,那双总是含笑的眼睛此刻像淬了冰。
她没有像对方预料中那样大吵大闹,反而深吸一口气,出奇地平静下来。
她从包里拿出纸笔,推到李主任面前。
“好,我理解。”她的声音清晰而冷静,“为了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请您把所有我们不能提、不能碰的‘禁止话题’,列一张清单给我。我们承诺,以后一定严格遵守,绝不越雷池一步。”
李主任愣住了,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回应。
这比歇斯底里的质问更让他难受,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却被棉花里的钢针扎了手。
他支吾了半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消息在团队内部迅传开。
苏霓看到那句“我没抢,可也没轮上”时,眼前一阵恍惚。
尘封的记忆被瞬间激活,她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电视台审片室。
那时,她刚入行,做了一期关于下岗潮的深度报道,结尾处,一位在寒风中等待零工的工人对着镜头,只说了一句:“工人兄弟不容易。”就因为这七个字,整期节目被总编以“传播负能量”为由,剪得面目全非。
那一夜,她写了一封长达五千字的申诉信,却最终没有勇气寄出。
此刻,苏霓从书房最深处的箱子里翻出了那份早已泛黄的信纸底稿。
上面的字迹还带着当年的不甘与愤懑。
她将底稿铺在桌上,又打开电脑,调出现行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相关条例。
她的手指在键盘上飞敲击,愤怒与不甘被转化为冷静而精准的法律条文。
一夜未眠。
第二天清晨,一份名为《社区口述史展示项目合规性操作指引》的文件诞生了。
文件中,苏霓用无可辩驳的法理逻辑明确提出:“个体记忆中的负面情绪,不等于对社会展的不良导向。”她甚至详细列举了十二种最常见的争议场景,如“个人遭遇不公”“历史事件创伤”“政策变迁阵痛”等,并为每一种场景提供了既能保留核心信息、又符合现行法规的合法表述建议。
她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而是将这份指引打印了整整一百二十份,以“市民建议”的名义,寄往了全市所有街道办事处。
在寄件人一栏,她用力写下:“一个差点不敢说话的人。”
与此同时,林晚在她的数据中心里,也开始了行动。
她没有去社区,也没有写信。
作为团队的技术和法务支持,她选择了最擅长的武器——规则本身。
她组织团队,对“银杏记忆角”所有被撤展板的原始素材进行了连夜复核。
结果很快出来:除了最核心的口述录音外,每一份展示材料,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字稿,都附有当事人亲笔签署的授权书,以及针对未成年人观看的明确回避声明。
所有程序,完美无瑕。
林晚没有将这份复核结果公之于众。
她深知,在某些规则体系里,公开抗议是最无效的手段。
她转而联系了一家与官方有长期合作关系的第三方社会工作评估组织,以项目委托的形式,邀请他们对“银杏记忆角”的全部内容及操作流程进行独立评估。
三天后,一份盖着钢印的评估报告出炉,结论措辞严谨而有力:“该项目在保障公众知情权与尊重个体隐私权之间取得了良好平衡,内容真实,形式温和,符合社区文化建设的积极方向。”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这份报告没有给媒体,也没有交给居委会。
林晚通过她在教育系统内的老同学,将报告的电子版悄无声息地上传到了市教育系统的内部资源库,并被几个相熟的文化部门朋友,转存进了内部决策的参考目录。
她要让那股“力量”在自己的体系内,看到一份来自“自己人”的专业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