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DU搜读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 第302章 闭嘴的时候心还在走(第2页)
第302章 闭嘴的时候心还在走(第2页)
数据分析冰冷而精准地显示,在过去四个月里,他仅仅上传过一次音频,内容是机械地抄读语文课文,没有任何个人情绪。
他的父母离异后双双外出务工,他独自一人在寄宿学校生活,害怕“说错话惹人烦”,于是选择了彻底的沉默。
林晚亲自带队,没有直接联系男孩,那只会加重他的恐惧。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她们联系了学校的广播站,在午间广播里插播了一段匿名录音。
那是一个有些紧张、但很真诚的声音:“我也很怕说话,怕被别人笑话。但我今天试了一下,录下了这段话,其实……好像真的没人笑话我。”
三天后,系统后台弹出一条新的上传记录。
那个男孩,上传了他的第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
他用还带着一丝颤抖的童音,朗读了冰心的散文《小桔灯》,在录音的最后,他用几乎微不可闻的声音,加了一句:“我想……也做一个能照亮别人的人。”
另一边,陆承安正在法庭上处理一起棘手的公益组织财产纠纷案。
对方律师言辞犀利,直指他们运营的“家庭录音角”项目缺乏商业模式,纯靠情怀支撑,绝无可能持续十年以上。
“情怀,是这个时代最廉价的奢侈品。”对方律师总结陈词,胜券在握。
陆承安没有急着反驳。
他只是平静地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当庭展示给法官。
“律师先生说得对,情怀确实无法支撑十年。”他顿了顿,声音沉稳而有力,“但制度可以。”
他手中的文件,赫然是省民政厅刚刚下的红头批复——同意成立“民间记忆保护中心”,并将其列为省级重点社会组织孵化项目。
文件的最后,名誉主任一栏,签着两个字:苏霓。
“情怀一旦落地,就成了制度。”陆承安说完,目光不着痕迹地扫过旁听席的角落。
苏霓正坐在那里,仿佛一个毫不相关的旁观者,低着头,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自己的袖口,嘴角却不易察觉地微微扬起。
榕城的梅雨季来临前,苏霓独自一人回到了最初启动项目的那个地方——榕城老年大学。
教室已经焕然一新,换上了更舒适的桌椅。
墙上,挂着一整面“银音频日历”的实体展板,每一张卡片都是一个老人的声音故事。
最新一期的标题是:“老张今天钓到了一条三斤重的大鲫鱼,可惜出门太急忘了带秤。”
苏霓像一个普通访客,悄悄坐在最后一排,听着新来的年轻志愿者讲解如何给录音添加背景音乐。
课间,一位白苍苍的老人颤巍巍地走到她面前,以为她是新来的老师,将一张写满了字的纸条递给她:“老师,我……我眼睛花,看不清,能帮我把我写的诗念出来吗?”
苏霓接过那张布满褶皱的纸,一如许多年前的那个午后。
她清了清嗓子,对着老人递来的录音设备,逐字逐句,清晰而温柔地朗读起来。
这段录音被系统自动编号为loooo,标题是老人自己起的:“她说的,还是我想说的。”
当苏霓起身离开时,满屋子的欢声笑语中,没有人知道,这位创始人刚刚回来过。
当晚,许文澜的办公室里,一声尖锐的系统警报划破了深夜的寂静。
她猛地从小憩中惊醒,看向屏幕。
一条最高级别的系统日志,以血红色的字体浮现:用户eoooo号,最后一次激活。
紧接着,一个标题缓缓弹出:“原来最安静的人,一直在最响地活着。”
屏幕中央,那串代表着苏霓的档案编号,状态瞬间更新为两个冰冷的汉字——已完成。
几乎在同一瞬间,从北国雪原到南海渔村,全国两千三百余个“家庭录音角”的终端设备,无论是否有人正在使用,都在这一分钟内,被一股无法抗拒的指令强行接管,自动播放起一段全新的音频。
没有激昂的音乐,没有深情的话语,只有长达十秒钟、清晰可闻的呼吸声。
那呼吸声平稳、悠长,仿佛在积蓄着最后的力量。
十秒后,一个熟悉到刻入骨髓的平静女声,通过亿万个扬声器,响彻在每一个角落。
“我是苏霓。从今往后,轮到你们说了。”
音频戛然而止。
所有终端的屏幕都在瞬间渐暗,只在中央留下一行白色的小字,如同黑暗中的萤火,缓缓浮现:
亮光不灭,因为它从来不在台上。
当晚,许文澜彻夜未眠。
eoooo号档案的状态更新为“已完成”,这三个字像一枚烧红的烙铁,烫在她的视网膜上。
系统日志里,在那条状态更新的千分之一秒后,紧跟着另一条她从未见过的、权限级别为最高的指令,正静静等待着被执行。
喜欢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请大家收藏:dududu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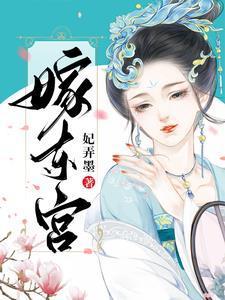
![病弱反派ooc了[快穿]+番外](/img/78069.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