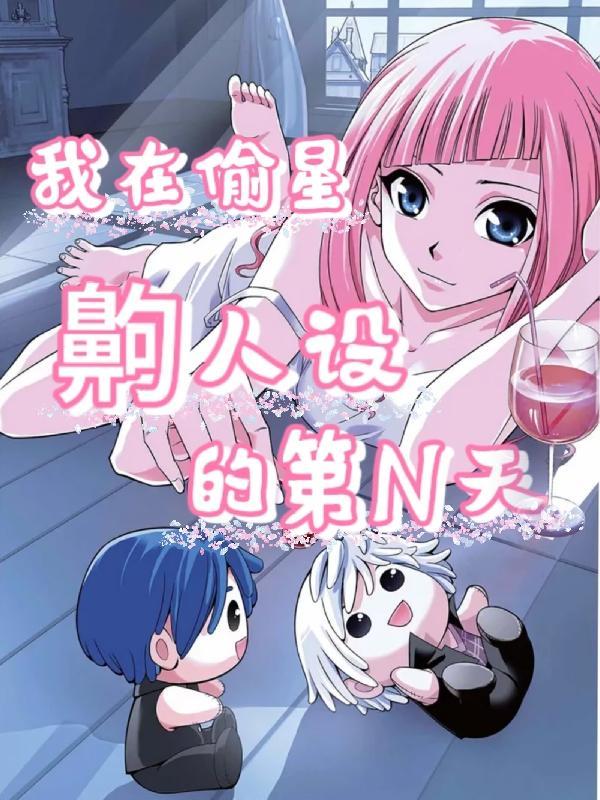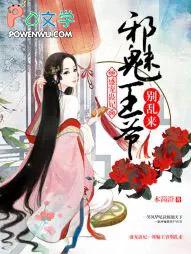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70年代:我一进山美女排队献身 > 第189章 足智近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第1页)
第189章 足智近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第1页)
捐款的狂潮,持续了两天半!
到第三天下午,当捐款办公室宣布截止时,账本上的最终数字,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七十八万六千三百元。
这个数字,加上李默之前投入的两万,以及姚和韵和一些干部职工的捐款,总额已经突破了八十来万了。
这笔钱,在后世看来或许不算什么,但在人均月工资只有几十块的八十年代初,对于一个贫困县来说,无异于一笔天文数字。
它不仅远远过了姚和韵最初的预期,甚至足以支撑整个清河县安然度过这个严冬,并且还有大量的结余,可以用于灾后的生产恢复。
消息传出,整个县城都沸腾了。
姚和韵亲自带着人,将崭新的“爱心模范榜”贴满了全县的每一个角落。
榜的名字不再是李默和姚和韵,而是变成了马德彪,鸿运运输队,捐款十五万元。
紧随其后的是王富贵,清河纺织厂,捐款十三万。
之前那份令人难堪的“光荣榜”,则被悄无声息地撕了下来,仿佛从未出现过。
那些曾经被千夫所指的老板们,一夜之间,又成了人人称颂的“大善人”、“爱心企业家”。
百姓们是淳朴的,他们不管过程如何,只看结果。
你掏了钱,救了大家的命,你就是好人。
马德彪的车队重新上路时,路边非但没人扔烂菜叶子了,甚至还有大爷大妈主动给司机递上热水和煮鸡蛋。
这就是李默想要的结局。
钱要拿到,人心也要稳住。
毕竟,这些商人未来还是县里经济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一棍子打死。
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名利双收的机会,远比把他们彻底踩死要高明得多。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
吴有钱就是那个例外。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中时,吴有钱的宅子里,却是一片死寂。
他的生意彻底停摆了。
没有一个工人愿意来上工,没有一个客户愿意跟他交易。
他就像一个孤岛,被整个清河县彻底孤立了。
他终于怕了。
他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他低估了民意的力量,更低估了姚和韵和那个叫李默的年轻人的手段。
在家里枯坐了两天后,他终于做出了决定。
吴有钱变卖了一部分家产,凑了足足二十万现金,装在两个大皮箱里,亲自提着,来到了县政府,点名要见姚和韵。
他以为,只要自己拿出的钱足够多,多到能碾压马德彪的十五万,他就能挽回这一切。
他不仅能重新夺回头把交椅,还能让姚和韵对他刮目相看。
甚至吴有钱过来捐钱的时候,还摆出了一副你大爷的气势!
然而,他在县长办公室的门口,被拦住了。
姚和韵的秘书,一个戴着眼镜的斯文年轻人,客气而疏离地对他说道:“吴老板,不好意思,姚县长正在开会,没时间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