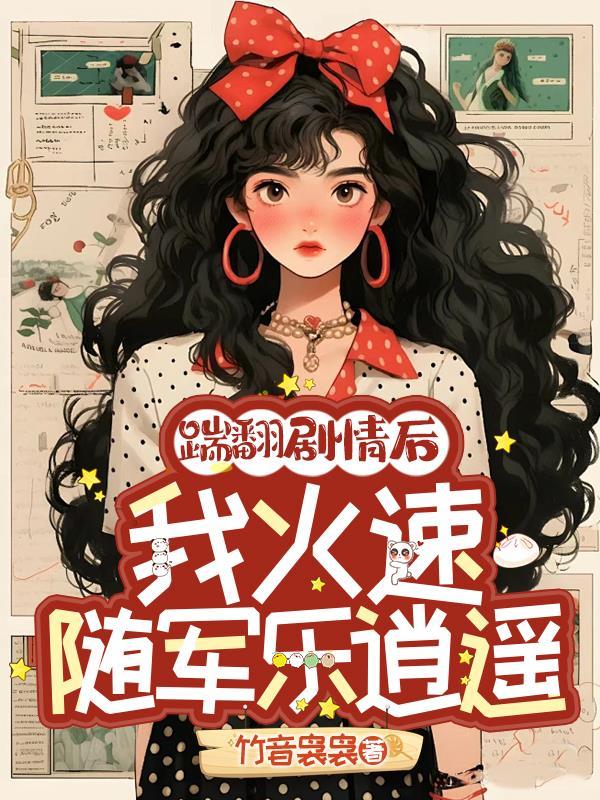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大唐修仙:李二求我当太子 > 第163章 为天子禁军培育绝对忠诚之骨干(第2页)
第163章 为天子禁军培育绝对忠诚之骨干(第2页)
众目睽睽之下。
李恪神色不变,反而唇角微扬,看向脸色紧绷的孔颖达,朗声说道:
“孔老大人方才所虑,是担心军校生同窗结党,形成武将集团,尾大不掉!”
“乃至重现东汉末年,至隋末军阀割据、皇权旁落之祸,是也不是?”
孔颖达见李恪主动提起这最尖锐的问题,脸上带着大儒的傲然与笃信:
“正是!正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师!此乃史鉴昭昭,殿下岂能不察?”
“在恪看来!”
李恪冷哼一声,大声呵斥道:“孔大人此虑,看似深谋远虑,实则是未能洞察根本,亦是……大谬!”
他这一声“大谬”,再次让满殿哗然,也让孔颖达的脸色瞬间阴沉如水。
“殿下?设立军校,难道不会破坏府兵?难道不会导致军阀割据?”
孔颖达反驳道。
李恪也不气恼,条分缕析,直指核心:
“孔大人所忧之割据,其根源究竟何在?”
“在于以往之将帅,或源于门阀世袭,或起于地方豪强,或出自士绅大族。”
“其兵,多为宗族、部曲演化而来,乃是私兵!”
“其将,权力基础在于家族或地域,实为家将!”
“故而!”
“将帅视军队为私产,士兵只知将帅,不知朝廷,此乃割据之土壤!”
李恪话锋一转,声音拔高,如同金石交击,瞬间响彻整个两仪殿:
“然,我大唐欲立之军校,截然不同!”
“其学员,乃是从天下良家子、有功士卒中公开选拔,不论门第,只重忠勇才略。”
“入校第一课,便是向陛下您宣誓效忠!”
“其次!”
“他们所学之兵法韬略,由陛下钦定之教材;他们日后所获之勋衔职位,皆出自陛下之天恩亲赐!”
李恪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定格在李世民身上,微微拱手,语气铿锵:
“如此,天下有志从军之才俊,其晋升之途,尽系于陛下之恩赏!”
“其忠诚之心,直接归于陛下之皇权!”
“他们心中唯有朝廷,唯有我大唐皇帝陛下,何来私恩?何来恩主?”
“此正是效仿当年汉武帝设立‘羽林郎’之深意——为天子禁军培育绝对忠诚之骨干!”
说到这里,李恪看向孔颖达,气势咄咄逼人:
“若天下精兵之骨干,皆出自陛下亲任校长的军校,皆为天子门生!”
“这非但不会形成割据势力,反而从根本上铲除权臣、割据产生的土壤!”
这一番剖析,如拨云见日,将“军校”与“割据”的因果关系彻底扭转!
许多原本担忧的官员,尤其是深知兵事的李世民,眼中爆发出精光。
“反观现今之府兵制!”
李恪趁热打铁,继续道:“战时临时委派将帅,兵不识将,将不知兵!”
“看似防范了武将,实则严重削弱了军队战力!”
“一旦遭遇战事!”
“朝廷仍不得不高度倚赖宿将之个人威望,及其麾下部曲来稳定战局。”
“敢问孔大人!”
李恪看向孔颖达,冷声质问道:“这种依赖于个人威望,私属力量的模式!”
“难道不更存在着‘因人成事、人去政息’的风险吗?难道不是真正的隐患吗?”
“故而,军校之制,正是要化私为公!”
“将军事人才的培养,从门阀私相授受、地方豪强把持的旧模式中解放出来,收归国家统一操办!”
“此乃集权于中央,强干弱枝,巩固国本之万世良策!何来割据之忧?”
![(排球少年同人)[排球少年]才不想做普通朋友!+番外](/img/23253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