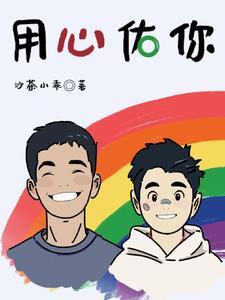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大唐修仙:李二求我当太子 > 第186章 程咬金 他娘的盛世不就来了吗(第1页)
第186章 程咬金 他娘的盛世不就来了吗(第1页)
孔颖达听到这里,缓缓摇头,不以为然:
“殿下善于举例!”
“老夫亦承认科举、三省皆有可取之处。”
“然,制度终为末节;人心道德,方为根本!”
“若仁义礼智信,不能深深扎根于万民之心,若无内在的道德自觉!”
“那么再精妙、再严密的制度,也终会被无穷的私心贪欲所腐蚀!”
“最终被腐蚀得千疮百孔,形同虚设!”
孔颖达旋即也举了例子:“商鞅变法,其法网之严密,刑罚之严峻,不可谓不极致,然秦之如何?”
“二世而亡!”
“此正是重法轻德,舍本逐末,导致人心尽失,社稷崩塌的明证!”
“殿下不可不察!”
“孔师所言极是!”
李恪微微拱手:“人心道德,确为万事之本,如木之根,水之源!”
“对于此,晚辈从未敢忘,更不敢轻视!”
李恪先恭维了一句,旋即话锋一转,道:
“故而!”
“晚辈浅见,于治国而言,教化与法制,二者非但不应相互排斥!”
“反而应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李恪面向李世民,又看向房玄龄等重臣:
“我大唐,尊儒重教,推广教化,便是在做‘固本培元’之功,使仁义礼智信等礼法深入人心!”
“同时!”
“我们亦需根据时代之需,因俗制礼,因时立法,不断完善律法、革新制度,划定权利与责任界限!”
“这便是法治‘强末’之举,为国家运行,提供清晰的轨道和保障。”
“这固本与强末!”
“这道德与制度!”
“正是我大唐不断前行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支撑,共同趋向完美的双翼!”
孔颖达听着李恪那“双翼”之论,虽觉新颖,却仍觉其过于理想化。
“殿下巧言善辩,老夫佩服,即便如你所说!”
孔颖达冷声道:“然史册昭昭,历历在目!”
“黄河决堤,水患肆虐,黎民流离失所!”
“北境烽烟时起,异族铁蹄叩关,将士血染黄沙!”
“朝堂之上,地方之间,贪官蠹役如同韭苗,割之不尽,此起彼伏!”
孔颖达有些痛心疾首的质询,目光锐利如刀:
“面对如此之多的‘不完美’,殿下口中那听起来美妙的‘动态完美’,又该如何自圆其说?”
“这难道不是无视现实疮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吗?”
这一问,极其尖锐!
将最残酷的现实问题,赤裸裸地摆在面前。
许多大臣暗自点头。
是啊,理想说得再好,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终究是空中楼阁。
面对这种近乎釜底抽薪的质问,李恪丝毫不慌。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抛出了两个看似不相干的反问:
“恪敢问孔老大人,这世间,可有一片从不起波澜的浩瀚大海?”
“可有永不遭遇风霜雨雪、雷电侵袭,而始终枝叶繁茂的万年松柏?”
孔颖达微微一怔,下意识回答道:“自是没有!”
李恪微微一笑,不再卖关子,目光灼灼道:
“黄河泛滥,是天灾,亦是‘不完美’!”
“然我大唐没有坐以待毙,更没有试图掩盖!”
“我们组织民力,修渠筑坝,疏浚河道,将肆虐的洪水化为灌溉良田的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