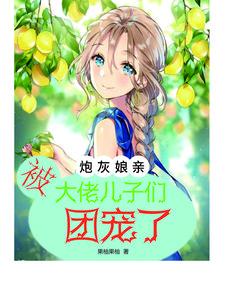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综影视:白浅被挖眼前觉醒记忆了 > 第13章 鲜儿改命记完(第1页)
第13章 鲜儿改命记完(第1页)
冬日,张家的杂货铺里,货架空了大半。张金贵蹲在炉子边,拿着火钳拨弄着几块劣质的煤核,火苗有气无力地窜着
“进不来货了,”张金贵的声音干涩,“关卡查得死紧,稍微像样点的东西,都说是‘军需物资’,扣下不说,弄不好还得进去吃官司。”
鲜儿没说话,把根生往怀里搂了搂。孩子的小脸冻得青,身上裹着好几层旧衣服,还是止不住地哆嗦。粮儿靠在墙边,搓着手,哈出的白气很快消散在冰冷的空气里。
铺子门被推开,带进一股刺骨的寒气。一个戴着破毡帽、脸颊冻得通红的男人闪了进来,是“老林”。他比以前更瘦,眼窝深陷,嘴唇干裂。
“老板娘,称半斤盐。”他的声音沙哑,手指冻得不太灵活。
鲜儿默默起身,从柜台底下拿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小布袋,里面是家里最后一点细盐。她称也没称,直接递过去。
“老林”接过,手指在柜台上快敲了两下,目光扫过空荡的货架和屋里瑟瑟抖的一家人,眼神黯淡了一下。他从怀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伪满币放在柜台上,低声道:“保重。”
说完,他转身就走,身影很快消失在门外的风雪里。
鲜儿看着那几张几乎买不到什么东西的纸币,心里沉甸甸的。她知道,“老林”他们现在的日子,肯定比他们更难。
夜里,风雪更大了。鲜儿把家里能盖的东西都压在了根生身上,自己和粮儿挤在炕的另一头,靠着彼此的体温取暖。
“鲜儿,”“老林”他们……还有盐吃吗?”粮儿在黑暗里忽然问。他现在似乎能模糊地感觉到,鲜儿让他送出去的东西,是给谁的。
鲜儿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嗯”了一声。
“那……他们比咱还冷吗?”
“……嗯。”
粮儿不说话了,过了一会,他往鲜儿身边靠了靠,小声说:“鲜儿,等开春,俺多干活,挣了钱,咱买粮食,也给他们送点。”
鲜儿心里一酸,伸手摸了摸粮儿粗糙的头。“睡吧。”她说。
第二天,鲜儿把家里最后那点压箱底的白面拿出来,掺了大量麸皮,烙了几张干硬的饼。她又找出张金贵一件破旧的厚棉袄,把自己的棉裤拆了,掏出里面已经板结的棉花,重新絮了絮,勉强加厚了一点。
“粮儿,把这个给‘老林’送去。”她把饼和棉袄包好,递给粮儿,“老地方。路上机灵点。”
粮儿接过包裹,用力点头,推开门扎进了风雪里。
张金贵看着儿子消失的背影,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他佝偻着背,走到院门口,望着白茫茫的天地,眼神空洞。
鲜儿站在他身后,看着公公仿佛一夜之间全白了的头,心里像压着块石头。这个家,已经被掏空了。可只要还能动弹,只要还有一口气,那条看不见的线,就不能断。
粮儿直到天黑才回来,帽子、眉毛上都结了冰霜,嘴唇冻得紫,一进门就瘫坐在门槛上,半天缓不过气。
“送……送到了……”他牙齿打着颤说。
鲜儿赶紧把他拉进来,用雪搓着他冻僵的手脚。粮儿缓过劲,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鲜儿:“‘老林’给的……说……说给根生……”
鲜儿打开,里面是几块拇指大小的、黑乎乎的糖块。在这年月,这是顶金贵的东西了。
她拿起一块,塞进眼巴巴望着的根生嘴里。孩子尝到甜味,眼睛立刻亮了。
鲜儿把剩下的糖仔细包好,藏起来。
很快,东北最难熬的冬日过去了,春天也过去了,很快又进入了夏季
鲜儿在柜台后给根生缝书包。孩子七岁了,该认字了。她没接话,心里却跟明镜似的。前几日“老林”深夜来过一次,没拿东西,只留下一句:“嫂子,再咬牙撑一撑,快了。”
快了。这两个字像小火苗,在她心里窜了这么多天。
八月中的一天,晌午头,日头毒得能晒化柏油路。街上忽然传来一阵异常的喧闹,夹杂着哭喊和听不清的叫嚷。张金贵猛地站起身,侧耳听着。粮儿也从后院跑进来,一脸茫然。
鲜儿放下针线,走到铺子门口,推开一道缝。只见街面上乱哄哄的,有些人疯了似的往家跑,有些人则聚在一起,激动地比划着什么。几个日本兵端着枪,想维持秩序,却被混乱的人群冲得东倒西歪,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仓皇。
“咋了?这是咋了?”张金贵紧张地问。
没人能回答他。混乱中,不知道是谁用尽力气嘶喊了一声,那声音穿透了嘈杂,清晰地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
“小鬼子投降了——!”
像是一道炸雷,劈在了闷热的天空上。街上瞬间死寂了一瞬,随即,更大的声浪爆出来。哭声,笑声,呐喊声,混成一片。
张金贵手里的蒲扇“啪嗒”掉在地上。他愣愣地站着,身子晃了晃,鲜儿赶紧扶住他。老人的嘴唇哆嗦着,浑浊的老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顺着他深刻的皱纹往下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