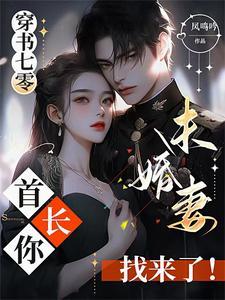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 第127章 她还没下令但所有人都跟着她改了步调(第2页)
第127章 她还没下令但所有人都跟着她改了步调(第2页)
可她不怕。
因为她早已明白,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站在聚光灯下被人称颂,而是让每一个曾被遮蔽的声音,都有勇气按下录制键。
就在此时,楼下传来邮差的脚步声。
老张从信箱取出一封信,信封泛黄,没有寄件人。
他拆开,里面只有一张旧照片。
年,纺织厂会议室,十几名工人围坐一圈,桌上摆着一台老式录音机。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他怔住了。
照片背面,有一行模糊的铅笔字迹,几乎难以辨认:
“我们录下了那天的话……你还记得吗?”老张的手指微微颤,指尖摩挲着那张泛黄的照片边缘。
年的光影仿佛穿透了三十年的尘埃,将他拉回那个闷热夏夜的纺织厂会议室——风扇嗡嗡作响,工人们脸上是愤怒与绝望交织的潮红,而他自己,缩在角落,手里紧握着一台老式录音机,像攥着一块烧红的铁。
“记录是为了不让历史睡着。”
那行铅笔字歪斜模糊,却如惊雷炸在他心上。
是谁寄来的?
那些曾被消音的声音,竟以这种方式苏醒?
他久久伫立窗前,雨丝打湿了半开的玻璃。
窗外城市灯火朦胧,像一片沉没在水底的记忆。
他知道,这张照片不是怀旧,而是一声召唤——一场跨越时代的交接。
次日清晨,省影像档案馆收到三封手写推荐信。
收件人是三位“夜间共述会”的青年志愿者:一个聋哑学校的老师,用视频手语收集残障群体口述史;一个快递员,在派件途中帮老人上传拆迁诉求;还有一个辍学少女,自学剪辑制作城中村生活纪实。
他们从未获奖,也未登台,只是默默把镜头对准了“不该被看见”的地方。
推荐信末尾,老张亲笔写下一句话:“真正的影像伦理,不在教科书里,而在他们颤抖却坚定的手上。”
落款处,一枚小小的波形图标悄然浮现——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民间录音运动的秘密标记,象征声音的流动与不灭。
与此同时,江城中级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外,人群已悄然聚集。
陆承安整理袖扣,步入庭审现场。
被告席上坐着那位被辞退的社区网格员,三十出头,眼神疲惫却倔强。
检方援引《基层治理信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未经审批,禁止录制并传播工作场景”,称其行为“扰乱公共秩序”。
“荒谬。”陆承安翻开证据袋,取出一段u盘,“那么请问,公民举报权、言论自由、监督权,是否也需要先向您申请许可?”
全场寂静。
他当庭播放了一段视频——画面中,苏霓站在听证会现场,白衬衫熨帖如刃,目光清冽扫过台下官员。
“我们建‘蜂巢节点’,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让那些本该被听见的声音,不必再翻墙、越级、跪信访局门口哭诉。如果连一个普通人录下自己家漏水的天花板都要被问责,那这个系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视频结束,法庭鸦雀无声。
陆承安缓缓起身,直视对方律师:“你说他在‘传播负面舆情’。可什么是负面?真实就是负面吗?当公民权利需要基层执行者冒职业风险才能实现,是我们走得太快,还是制度太慢?”
法官沉默良久,最终宣布休庭。
雨还在下。
细密如织,敲打着法院外墙的梧桐树。
一位年轻书记员抱着案卷走过走廊,低声问身旁同事:“那个试点项目……什么时候能覆盖到我们这儿?”
没人回答。
但所有人都知道,某种变化正在生——像春汛潜行于冻土之下,无声,却不可阻挡。
同一时刻,一份名为《关于推进全域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的建议方案》静静躺在省委办公厅流转桌上。
署名栏空着,没有主动呈报,也没有催促批复。
而在千里之外的某座小城车站,一辆破旧中巴驶入棚户区深处。
车门打开,一名穿着洗得白牛仔外套的女人跳下台阶,肩背双肩包,径直走向一栋即将拆除的老楼。
楼道里霉味弥漫,墙上还留着“拆”字的红漆印记。
她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轻轻推开了门。
喜欢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请大家收藏:dududu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