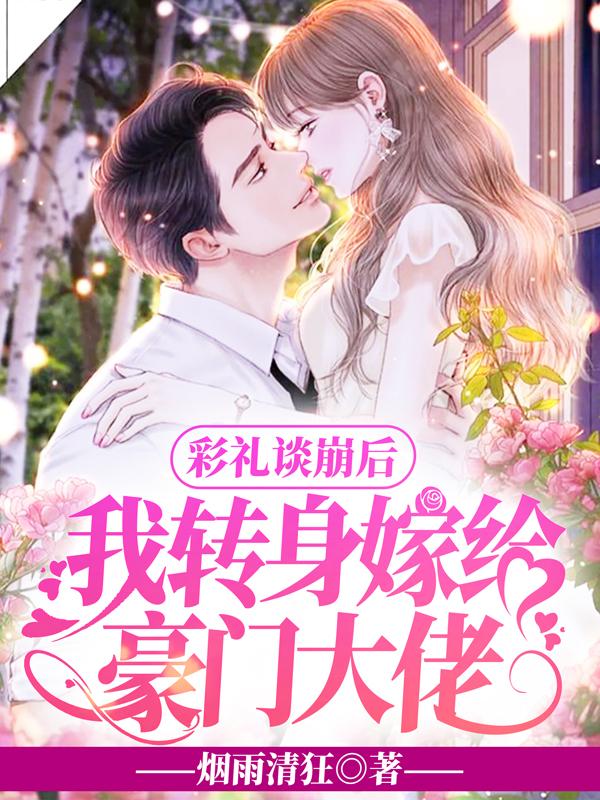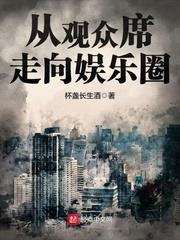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 第191章 种下去的名字开出了路(第1页)
第191章 种下去的名字开出了路(第1页)
风暴来临前的空气,凝滞得如同固体。
数字世界里,另一场风暴正以亿万次的计算度,呼啸着席卷而来。
许文澜的指尖在键盘上敲出一行行冰冷的指令,她面前的屏幕上,一张覆盖全国的地图正被无数闪烁的数据点重新定义。
这不再是简单的“沉默代价地图”,而是它的升级版——一个接入了气象、地质甚至人口流动模型的恐怖预测系统。
她要做的,不是记录已经生的悲剧,而是预判悲剧将在何处滋生。
突然,系统出一声尖锐的警报。
内蒙古,一个人口稀疏的旗县,数据异常得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近三年,竟有四十六名已被官方系统标记为“死亡”的人员,仍在持续不断地领取低保!
更诡异的是,这些“幽灵”的登记住址,全都指向同一个坐标——一处早已废弃多年的劳改农场。
心脏猛地一缩,许文澜仿佛透过屏幕看到了那片荒原上空盘旋不散的冤魂。
她没有丝毫犹豫,迅将所有线索、数据模型和分析结果加密打包,伪装成一份普通的高校社会学研究项目合作邀请,通过一个绝对安全的渠道,转交给了当地一位以死磕硬骨头着称的公益律师。
她深知,直接以国家记忆馆的名义介入,只会激起地方系统的强烈抵触,打草惊蛇。
她要做的,是在千里之外,为前线的战友递上最锋利的刀。
与此同时,一场无声的革命正在街头巷尾悄然萌芽。
林晚在对无数份“留痕土”样本进行分析后,终于总结出了它的传播路径——“三阶渗透模型”。
第一阶,是个体最私密的哀悼,是亲人离去后,不愿洗去的血迹、不愿丢弃的烟头。
第二阶,是家庭内部的传承,是子孙将这些痕迹混合着故乡的泥土,作为一种无声的传家宝。
第三阶,则是社区的共鸣,当足够多的家庭拥有了这份沉重的“传家宝”,它们便汇聚成了公共的记忆。
理论必须化为行动。
林晚不眠不休,编写了一本名为《非语言记忆重建手册》的小册子。
她用最朴素的语言和最直观的图画,教导人们如何识别、采集、转化身边那些承载着记忆的日常痕迹。
手册印五千册,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被悄悄送往各地的老年大学和社区书屋。
结果乎想象,三个月内,这本免费的小册子被自翻印过两万份。
许多城市的街角、公园里,开始出现一个个小小的“家门口的记忆角”,人们用玻璃瓶装着从自家阳台、旧屋墙角刮下的“留痕土”,旁边贴着一张小纸条,写着一个名字,一个日期。
民众的情绪像一堆干柴,只差一颗火星。
赵小芸点燃了它。
她通过所有能动用的社交媒体渠道,起了一场名为“百城共写一日”的活动。
时间,定在o月日,那个曾经只属于铜岭市的伤疤——矿难纪念日。
她没有设立任何统一的主题或口号,只号召所有愿意参与的人,在那一天,用粉笔、蜡笔,甚至是有色胶带,在任何安全的公共墙体、广场地砖或设施上,标记一句最想让这个世界听见的话。
那天,从冰封的漠河到湿热的三亚,过三百座城市爆了前所未有的书写潮。
城市变成了巨大的留言板。
“我还活着”“我爸没疯,是他忘了吃药”“我们没同意拆迁”“李医生,谢谢你”……这些简单而刺骨的句子,覆盖了天桥的桥墩、公园的长椅、废弃工厂的外墙。
出人意料的是,往日里雷厉风行的城管队伍,这一次却选择了沉默。
甚至在一些城市,当傍晚的雨水开始冲刷字迹时,有陌生人默默走上前,撑开一把伞,为一个陌生的名字挡住冰冷的雨滴。
民意如沸,陆承安顺势而为,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一份石破天惊的议案——《关于设立国家记忆日的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