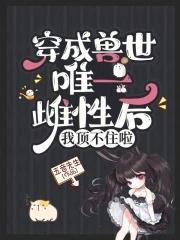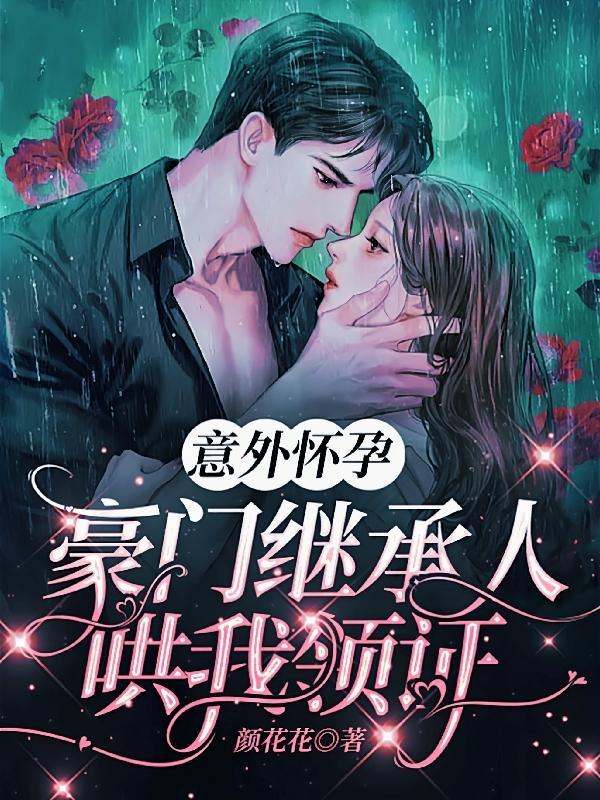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 第219章 风起时谁在记名字(第2页)
第219章 风起时谁在记名字(第2页)
镜头前,赵小芸像一个经验丰富的主持人,引导着话题。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起初,老师还很拘谨,家长也只是重复着担忧。
但随着对话的深入,气氛渐渐改变。
老师谈到了自己作为教育者的初心,家长谈到了家族几代人无法言说的隐痛。
最后,赵小芸把镜头对准了那个写出满分作文的女孩。
女孩有些紧张,但眼神清亮。
她拿出作文本,用还带着稚气却异常坚定的声音,朗读了自己未经任何删改的原文。
当读到结尾时,她的声音微微颤抖,却无比清晰:
“……所以,我写下这一切,不是在撕开家族的伤疤,给谁难堪。我是在缝合它。用我这一代人的笔,一针一线,把它缝合成我们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我不是在揭伤疤,是在缝合它。”
这句话,仿佛一道闪电,瞬间点燃了整个网络。
直播间人数从几千飙升到几十万,弹幕如瀑布般刷屏。
这句话,成了无数人心中郁结的完美表达,一个响亮的宣言。
几乎在同一时间,林晚的邮箱里,也涌入了一批特殊的投稿。
它们来自更遥远的边疆地区,记录着一群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政审问题”被注销户口、成为“黑户”的边缘群体的现状。
这些记忆粗糙、朴素,却字字泣血。
其中一封信的附言,让林晚看到深夜,再也无法入眠。
“我们这代人,不求什么平反了。我只希望,等我孙子将来长大了,去报考军校、想当个保家卫国的兵时,政审表‘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那一栏里,别再写上‘祖上有疑’这四个字了。”
跨越半个世纪的卑微祈求,像一记重锤,砸在林晚的心上。
她通宵未眠,将这批材料一份份分类、归档,在文件夹的命名上郑重地敲下——“跨代际影响案例集”。
第二天一早,这份沉甸甸的档案,被她提交至基金会的政策研究组,并附上建议:将其纳入即将召开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研讨会的正式议题。
线上的舆论在呐喊,线下的材料在集结,而最高层的博弈,则在无声处进行。
法工委的一间小型会议室里,气氛严肃。
陆承安作为特邀代表,面对几位对户籍制度改革持保留意见的部委官员,他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去陈述那些“历史遗留问题”的悲情故事。
他只是打开投影,展示了一组冷冰冰的法律逻辑推演。
“各位领导,我们假设十年后,第一批因‘历史身份空白’而无法继承数字遗产、无法进行基因溯源、甚至无法享受某些新兴公民权利的诉讼案出现。届时,我们的《民法典》《行政诉讼法》将找不到任何一条明确的救济路径。法庭将陷入巨大的伦理和法理困境。”
他平静地看着众人,语气没有丝毫起伏,却带着一种不容辩驳的穿透力:“我们可以选择现在被动地应对一场场注定会生的社会危机,也可以选择现在主动地去建构一个能容纳这些问题的法律框架。前者是裱糊匠,后者是建筑师。”
满室寂静。
会议结束后,一位头花白的资深委员在走廊上叫住了他,看似随意地问道:“承安,说句私下的话,你们那个‘银杏基金’……背后到底是谁在撑腰?这股劲儿,不像是一般的民间组织。”
陆承安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回答。
一周后,所有的努力汇成了一股看得见的巨流。
《中国教育报》头版转二版的位置,刊了一篇题为《让青春之笔书写真实》的署名评论文章。
文章不仅正面肯定了“写真实”的价值,更罕见地大段引用了西南边陲那位满分女孩作文的片段。
苏霓买了一份报纸,仔仔细细地从头读到尾。
当她翻到最后一页,看到编者按里夹杂的一句不起眼的话时
“有些声音,最初听起来像是风,后来才现是时代的回响。”
她轻轻合上报刊,窗外,一场蓄积已久的暴雨终于倾泻而下,洗刷着整座城市。
雨声中,她拨通了许文澜的电话,声音清晰而坚定:
“文澜,启动‘银杏计划’第二阶段——把这股风,吹进中小学历史教材的审查委员会里去。”
电话那头,许文澜应了一声。
就在她准备调出相关资料库的瞬间,她电脑屏幕一个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一个由她亲自编写、理论上绝不可能被外部触的底层监测程序,突然跳出了一行极细的红色警报。
警报没有声音,没有弹窗,只是安静地闪烁着,内容简单到诡异。
那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坐标,和一个倒计时。
喜欢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请大家收藏:dududu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