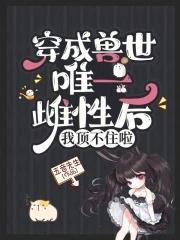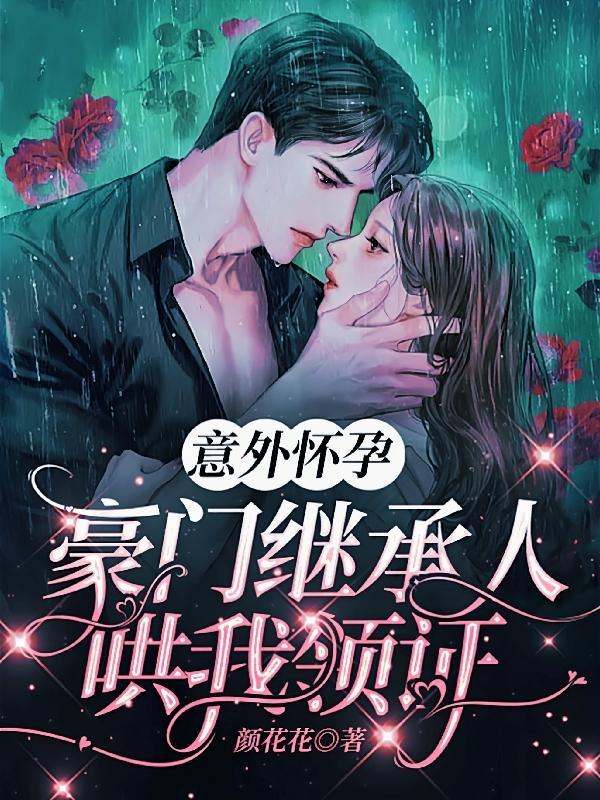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 第219章 风起时谁在记名字(第1页)
第219章 风起时谁在记名字(第1页)
那行黑色小字,像一枚楔子,钉入了所有人心照不宣的平静。
教育部官网深夜布的《关于高考作文评分标准的补充说明》里,那句“鼓励考生结合真实社会经历表达独立思考”像一束强光,而紧随其后的附注——“涉及历史遗留问题应把握分寸”,则是一团摇曳不定的阴影。
天台上,苏霓盯着手机屏幕,嘴角反而勾起一抹极淡的冷笑。
“这是怕出事,又不敢拦。”她低声自语,眼中却燃起了兴奋的火光。
这模糊的措辞,不是铁壁,而是裂缝。
是官方在汹涌的民意面前,一次试探性的、充满矛盾的退让。
而对于她们这群蛰伏已久的人来说,裂缝,就意味着整个堤坝的崩溃有了可能。
她没有丝毫犹豫,指尖在加密通讯软件上飞敲击,一个名为“银杏”的群组瞬间被激活。
“紧急线上会议,三分钟后开始。”
命令出,苏霓转身走进室内,身后猎猎作响的晚风仿佛成了这场无声战役的号角。
三分钟后,四个头像准时亮起。
“都看到了?”苏霓开门见山,声音冷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看到了。”赵小芸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这算是……半个好消息?”
“不,这是最好的消息。”苏霓纠正她,“一份畏缩的许可,比一份强硬的禁令更有价值。它证明,他们怕了。”她顿了顿,目光转向代表赵小芸的头像,“小芸,你的任务最重。立刻去整理这几天网络上所有能找到的高分作文,尤其是那些引起巨大反响的。我要你无视文采,无视立意,只提炼它们的共性叙事结构。我预感,会是一种模式。”
她伸出三根手指:“身份的缺失,家庭的创伤,最终指向制度的修复。把这个‘三段式’结构给我做成一个清晰、易于模仿的模板。这会是我们下一阶段公众倡导的‘弹药’。”
“明白!”赵小芸立刻领命。
与此同时,身处另一座城市的许文澜,指尖正在键盘上敲出一片残影。
她没有去关注官网,而是潜入了更深的水域。
几分钟内,一份加盖着“内部传阅”红戳的省级教育考试院文件,出现在她的加密服务器里。
文件要求,所有评卷组对“敏感题材”作文实行双人复核,并根据内容标记“a、b、c”三个风险等级。
许文澜的眼神冷了下来。
这才是那句“把握分寸”在执行层面的真实含义。
她没有停下,沿着文件的数字签名顺藤摸瓜,很快追踪到一个ip地址,指向一位刚刚退休的老干部。
资料显示,此人正是十几年前地方户籍改革的主要阻力代表之一。
曝光他?
不。
许文澜从不做这种一次性的消耗。
愤怒是廉价的,数据才是武器。
她将近五年来该省所有高考作文的平均分、高分段占比,与同期网络上关于户籍、历史身份等话题的舆情热度指数进行交叉对比。
数据被导入她亲手编写的模型,一行行代码飞滚动,最终,一份名为《舆情压力与评分偏差相关性报告》的pdf文件悄然生成。
报告用冰冷的数据雄辩地证明:每当相关社会议题热度升高,同类题材作文的平均分就会出现非正常下滑,高分率更是断崖式下跌。
这无关文笔,纯粹是评分者无形的自我审查。
许文澜看了一眼报告末尾那根陡峭的曲线,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
她没有将其公之于众,而是从通讯录里找出三个名字——三位长期参与国家立法咨询的顶尖法学专家,将这份报告用匿名邮件,悄无声息地推送到了他们的私人邮箱。
她要让子弹飞进真正能改变规则的地方。
风暴的中心,却远比想象中来得更快。
赵小芸刚刚完成模板的初步框架,一个来自西南边陲小城的陌生来电就打了进来。
电话那头,一位父亲的声音焦灼而无助,他告诉赵小芸,女儿的班主任被当地教育局约谈了,理由是“引导学生写作不当内容”,可能影响年度评优。
赵小芸的血液瞬间冲上头顶。
她知道,这是地方上最常见也最有效的施压方式——不针对你,而是针对你身边的人。
“您别怕,把手机给您女儿,我跟她说几句。”赵小芸的声音瞬间沉静下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挂断电话后,她抓起车钥匙和一套便携直播设备,没有片刻耽搁,驱车重返那个她刚刚离开不久的县城。
第二日下午,县城中学的校门口,一场史无前例的直播开始了。
赵小芸没有堵门,没有抗议,只是在操场的一角,架起手机,邀请那位满脸愁容的家长、被约谈后惴惴不安的班主任,以及几个闻讯而来的学生和老师,围坐在一起。
直播的标题简单直接:“我们为什么敢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