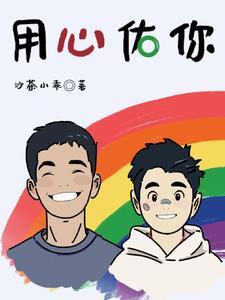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 第235章 谁在给标准盖章(第1页)
第235章 谁在给标准盖章(第1页)
空气仿佛在瞬间凝固。
许文澜的指尖停留在触控板上,屏幕上那份名为《关于设立“国家口述历史档案认证中心”的内部征求意见稿》的文件,字字都像淬了冰的钢针。
她的瞳孔骤然一缩,目光死死钉在那张组织架构图上。
省级档案局垂直管理,所有民间采集数据必须经其审核,方可入国家级数据库。
而在那密密麻麻的方框中,他们呕心沥血建立的“记忆方舟”基金会,被轻描淡写地安置在最末端,标注着一行小字:协作单位。
没有表决权,没有主导权,甚至没有建议权。
这意味着,他们将被彻底架空,沦为免费的数据搬运工。
许文澜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头的怒火,迅在文件上用红色高亮标记了五个字:“程序架空风险”。
她没有丝毫迟疑,开启追踪模式,几分钟后,一个名字浮出水面——起草组负责人,王宗明,一个从老牌地方史志办按部就班升上来的干部,以保守和强调“血统纯正”着称。
一场无声的风暴正在酝酿,而风暴眼中的苏霓,却异常平静。
接到许文澜的加密急报,她没有召集众人开会痛斥,更没有公开表示任何反对。
她只是出了两条简短而决绝的指令。
第一条,对内:“即刻起,暂停基金会所有对外合作意向项目,所有精力转向内部数据优化。”
第二条,对林晚:“启动‘沉默验证行动’。”
林晚秒懂。
她立刻将“记忆角”数据库的高级查询权限,通过加密通道,秘密开放给了五位正在参与相关立法咨询的顶尖法学专家。
没有引导,没有说明,只附上了一句简单的话:“欢迎自由检索,所有案例均可追溯原始链路。”
这五位专家,代表着法律界对“证据有效性”的最高判断。
其中一位专攻身份法的老教授,对基金会的数据一直持保留态度。
他抱着挑刺的心态,随意检索了一桩六十年代因政治原因被注销户籍的“黑五类”后代档案。
系统瞬间弹出一条主线,关联着三份看似毫不相干的旁证:一份是当事人在东北农场的劳动工分记录,一份是其邻居在八十年代初回城时写的旁证材料,还有一份,竟然是远在西南边陲的亲属,在迁移户口时填报家庭关系的一页模糊影印件。
三份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年代、不同来源的零散信息,被系统背后强大的算法严丝合缝地链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无可辩驳的证据链。
老教授对着屏幕,足足愣了半分钟,才拨通了助理的电话,语气里满是无法抑制的震惊:“他们……他们连这种跨越半个世纪的陈年纸屑都能串起来?!”
与此同时,赵小芸接到了她的任务。
一台高性能电脑前,她正飞剪辑着一段模拟推演短片。
画面一边,是标着“新中心单点审批模式”的流程图。
一个希望恢复知青身份的后代,从提交申请开始,文件需要在乡、县、市、省四级档案局之间层层流转,每一次审核、盖章、复核,都意味着漫长的等待。
屏幕下方,一个计时器飞跳动,最终定格在“预计耗时:个工作日”。
画面另一边,是基金会的“分布式系统”。
申请提交的瞬间,系统自动向全国数据库出匹配请求,二十四小时内,三条分别来自不同知青点的旁证链被同时激活。
四十八小时内,交叉验证完成,身份初步核实报告生成。
赵小芸将这段对比强烈的视频,剪辑成了一段冲击力极强的o秒精华版。
她没有加任何煽情的配乐,只有冰冷的数据和流程对比。
最后,黑屏之上,浮现一行血红的大字:《慢六个月,一个人就没了》。
视频没有公开布,而是通过加密邮件,精准地投送到了几位长期关注老龄群体权益的人大代表的秘书处邮箱。
这无异于在平静的湖面下,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
陆承安则在另一条战线上撕开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