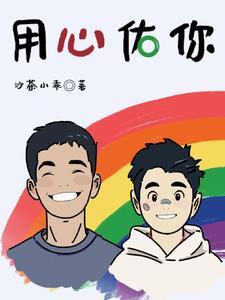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 第245章 你听春天在敲门(第2页)
第245章 你听春天在敲门(第2页)
他对着一个老旧的平板,用高棉语讲述了一段关于祖母在稻田里躲避战火的故事。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当系统自动将他的语音转化为文字,并根据他的手绘线条生成一份可视化的“记忆地图”时,这个年轻人的眼眶红了。
他激动地抓住许文澜的手,语无伦次地说:“天啊……我们的乡村教师……他们终于不用再靠纸和笔,一点点去记录那些快要消失在风里的故事了!这……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回国后不到一周,这位技术员便向苏霓团队来邮件,他们已迅组建了本地化团队,并为他们的项目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稻穗计划”。
然而,当苏霓团队开始筹备第一批海外培训讲师时,负责培训体系的赵小芸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
她推掉了所有专家和教授,反而从浩如烟海的记忆库中,调出了三个特殊的档案。
“教别人怎么倾听的人,必须是先被真正倾听过的人。”赵小芸的理由简单而坚定。
她推荐的三位“前记忆委员”中,赫然包括了oooo号种子库里,那个曾经孤僻寡言的留守儿童。
如今,少年已经长成了一个挺拔的青年。
在机场,面对前来送行的赵小芸,他深深鞠了一躬,目光清澈而郑重。
“赵老师,谢谢您。”他顿了顿,认真地说,“当年,您教会我的,不是怎么去说话,而是让我第一次相信,我说的话,原来是有力量的。”
赵小芸看着他登机的背影,眼角湿润。
她知道,这才是“银杏新芽”最核心的秘密——力量的传递,不是自上而下,而是从一颗被听见的心,到另一颗渴望被听见的心。
档案室里,林晚正在做最后的交接归档。
在整理那沓厚厚的申报材料时,一封夹在其中的信件吸引了她的注意。
信纸是小学生的作文本,字迹歪歪扭扭,却异常用力。
信里写着:“我奶奶说,打仗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女孩,每天都躲在地窖里。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见雨滴敲在泥土顶上的声音,咚,咚,咚……她说,那声音就像有人在外面敲门,可她永远不敢开。现在,我用手机录下了我们家屋檐下的雨声,放给她听。我想告诉她,奶奶,你听,春天真的会来敲门的。”
林晚的手指微微颤抖。
她小心翼翼地将这封信扫描进系统,在记忆库中为它建立了一个新的编号:oooo。
在标签栏里,她沉思良久,最终敲下了五个字:“光的传递者”。
送别代表团的当晚,喧嚣散尽,苏霓没有回家,而是独自驱车回到了最初的那个试点中学。
夜色下,校园里那棵巨大的银杏树静静伫立,十年光阴,它已枝繁叶茂。
树下,不知何时建起了一座小小的、玻璃外墙的微型展览馆,里面陈列着十年来最动人的口述史片段精选。
她驻足片刻,正准备转身离去,眼角的余光却瞥见树根处有两个小小的身影。
是两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正蹲在地上,用粉笔认真地在石砖上描摹着刻在那里的两个字——记得。
年幼一些的那个女孩仰起头,奶声奶气地问:“姐姐,我们一遍遍地写,要是以后还是没有人来看,怎么办呢?”
年长一些的女孩没有停下手中的粉笔,头也不抬地回答:“那我们就去教更小的小孩写。我们教他们,他们再教他们的弟弟妹妹。”
苏霓的心,被这稚嫩而坚定的回答轻轻撞了一下。
她没有上前打扰,只是默默地转身,在夜色中悄然离去。
这一刻,她比任何时候都确信,这颗种子,已经拥有了属于它自己的生命。
坐进车里,手机轻轻震动了一下。
是陆承安来的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他办公室的书桌一角。
一只从柬埔寨带回的、古朴的陶罐里,斜插着一截刚从银杏树上剪下的枝条。
枝条的顶端,一片娇嫩的黄绿色新芽,正迎着灯光,努力绽放。
苏霓的嘴角,终于漾起一丝疲惫而满足的微笑。
第二日清晨,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办公室里洒下斑驳的光影。
苏霓泡了一杯热茶,开始翻阅堆积在桌上的地方教育简报,这已是她多年雷打不动的习惯。
她的指尖在纸页上平稳地划过,一行,又一行。
当她的指尖划过一条来自中部某县城的报告时,动作倏地一顿。
她的瞳孔,微微收缩。
喜欢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请大家收藏:dududu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