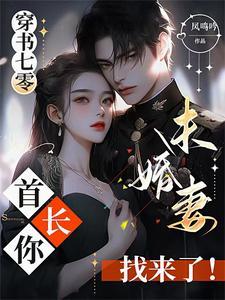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 第286章 静音区响了第一声(第1页)
第286章 静音区响了第一声(第1页)
o号文件夹的幽光,如同监控中心里一颗执拗的心跳,在死寂的屏幕上闪烁了整整四十八个小时。
这串代码,像一个来自深渊的叩问,无人应答,也无人敢于应答。
按照最高操作规程,任何过二十四小时未处理的a级警报,都应直接上报至记忆馆最高决策层。
但林晚没有。
作为苏霓最信任的副手,林晚比任何人都清楚,s系列文件夹的权限,仅对苏霓一人开放。
贸然上报,等于将苏霓最隐秘的角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她深吸一口气,指尖在权限申请的边缘悬停,最终却转向了另一个入口——苏霓近五年的个人行为模式数据库。
一串串数据流在林晚眼前飞划过。
她看到,每当记忆馆有重大项目突破,或遭遇巨大舆论压力时,苏霓的行为轨迹都会出现两个固定的锚点:要么,是驱车前往三十公里外的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在校门口那棵巨大的银杏树下静坐;要么,是独自在深夜的中央控制室,反复调试那段编号为ooore的空白声纹。
前者是她童年记忆的遗址,后者是她内心噪音的具象。
林晚的瞳孔骤然收缩,一个大胆的推论在她脑中成型:s系列根本不是什么冷冰冰的档案,它们是苏霓为自己埋下的“心理坐标”!
每一份s档案,都对应着她一段无法独自面对的创伤记忆。
而o的自动激活,意味着现实世界中,有什么东西触碰到了这根深埋的引线。
她不能再等了。
林晚绕过所有官方渠道,直接拨通了技术部席架构师许文澜的私人通讯。
“文澜,我需要你帮我做个东西,一个‘延迟唤醒系统’。”林晚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力,“s系列不能再这样被动触。我希望,每一卷磁带的开启,都需要一个‘钥匙’,一个只有苏霓能给予,且必须在特定条件下才能生成的钥匙。”
通讯那头沉默了片刻,许文澜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的兴奋:“你的意思是……生物特征识别,加上外部事件触?”
“对!”林晚的思路愈清晰,“比如,她的指纹,加上系统捕捉到她明确的情绪波动,再加上……一个相关的现实事件作为引子。三者合一,才能解开封印。”
许文澜沉吟了几秒,仿佛在脑中构建着庞大的代码框架,最后,他一字一顿地回答:“明白了。我们不能强行打开一扇尘封的门,但我们可以让它像心跳一样,由现实的回应来启动。”
一周后,一套名为“共鸣解密协议”的系统悄然上线。
许文澜带领他的精英团队,为每一份s系列档案都设定了三道严苛的解锁门槛:一,苏霓本人的指纹或虹膜验证;二,当日上传至记忆馆数据库的公众录音中,出现与该档案核心主题相关的关键词;三,系统实时监测到苏霓的生理心率,波动过个人基准值的百分之五。
林晚决定进行一次极其冒险的测试。
她从基层信息部门调取了一段刚刚上传的录音,内容是一位派出所民警对“走失儿童”案件的常规汇报。
她将这段录音标记为高优先级,然后,在苏霓例行巡视中央控制室,将手掌按上验证面板的那一刻,点击了上传。
嗡——
o的闪烁频率陡然加快,屏幕中央不再是单调的警报,而是跳出了一行冰冷的黑体字。
“年冬,棉纺厂女工张玉兰,寻女第七百三十一天。”
一行字,如同一把生锈的钥匙,撬开了历史的一角,却又戛然而止。
林晚知道,协议生效了。
她将测试报告和整套“共鸣解密协议”的构想原原本本地呈交给了苏霓。
苏霓看完报告,久久没有说话。
林晚站在她面前,甚至能听到自己因为紧张而过的心跳。
她以为会迎来一场风暴,但苏霓只是抬起头,眼底没有责备,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一丝……解脱。
“做得很好,”苏霓的声音有些嘶哑,“把调试权限也开放给我。这个系统,我亲自参与。”
从那天起,苏霓的生活多了一项内容。
她开始有意识地接触那些可能触s档案的现实场景。
半个月后,她受邀参观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在一间明亮的教室里,她看到一个约摸七八岁的听障小女孩,正用稚嫩的手语,一遍遍地向老师比划着同一个问题。
苏霓不懂手语,但她看懂了那双眼睛里的执拗和迷茫。
她问身旁的校长:“她在问什么?”
校长叹了口气,轻声说:“她在问,‘我想知道妈妈为什么不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