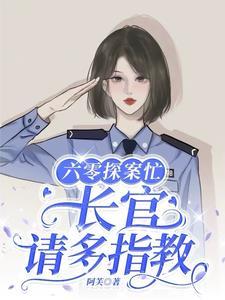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 第293章 无声之声奖(第1页)
第293章 无声之声奖(第1页)
清明前夜的雨丝,细密如针,悄然织进榕城的夜色里。
苏霓独自驱车,穿过霓虹浸染的街区,最终停在了师范附小那片沉寂的老校区前。
车轮碾过湿漉漉的落叶,出轻微的沙沙声,像一个被遗忘的叹息。
这里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斑驳的教学楼被改造一新,挂上了“社区文化中心”的牌子,唯有操场中央那棵老银杏树,依然固执地伸展着虬结的枝干,仿佛一位沉默的守望着,见证了无数代人的聚散离合。
苏霓撑开伞,一步步走向那棵树。
雨滴敲打在伞面上,奏出单调而规律的节奏。
她在树下的长椅上坐下,冰凉的触感从身下传来,却让她纷乱的思绪瞬间沉静。
她从随身的老旧帆布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台方方正正的磁带录音机。
机身已经磨损,边角泛着白,那是属于上个世纪的产物。
她深吸一口气,按下那个鲜红的“录音”键。
机器内部的齿轮轻微转动,出细不可闻的嗡鸣。
可她却迟迟没有开口,只是静静地望着眼前被雨水冲刷得愈青翠的草地。
千言万语堵在喉咙,最终却凝结成一片沉重的寂静。
一个穿着社工马甲的年轻女孩路过,看见这一幕,脚步一顿,随即笑着走近:“老师,您这机器可真是老古董了。现在我们都用防水的收音设备,放进保护套里,多方便。”
苏霓抬起头,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的浅笑,雨夜的灯光映在她眼底,泛起柔和的光。
“是啊,太老了。”她轻声说,目光重新落回那台录音机上,“我就是想试试,用最老的办法,还能不能……留住一句话。”
那女孩似乎被她话里的怅然触动,没再多言,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便转身走进了文化中心。
最终,苏霓什么也没说。
她只是坐在那里,任由录音机将风声、雨声、远处车流的呼啸声,以及银杏树叶被雨水打湿后簌簌的沙响,一并收录进去。
十几分钟后,她按下了停止键,将这段只有自然声响的音频,通过手机上传到了“日常回响”的个人栏目里。
在标题栏,她沉默了许久,最终只敲下了四个字:我在听着。
深夜,回声回路数据中心依旧灯火通明。
林晚作为席技术官,正在进行最后的系统巡检。
当她看到苏霓的最新上传时,不由得愣了一下。
这是苏霓宣布退隐后,极少数的私人动态。
她立刻调取了这段音频的情感波动曲线,屏幕上,那条代表情绪的线条平稳得近乎一条直线,只在末尾处微微上扬,系统标注为——“释然”。
一个如此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空洞的音频,却透着一股奇异的安抚力量。
林晚的指尖在屏幕上轻轻划过,另一组数据让她心头一震:“回声回路”应用程序的后台显示,在过去一周内,共有名用户设置了“等待苏老师回应”的特别提醒。
一千八百多个孤独的灵魂,在深夜里,等待着一个来自传奇的微弱回响。
林晚没有声张,更没有利用苏霓的名气去做任何宣传。
她只是沉思片刻,编写了一段简单的代码。
她将这段混合着风声与树叶沙响的音频,设置为所有指向苏霓的联系请求的夜间自动回复。
从此,每当有人在深夜试图联系那个已经退隐的“声音疗愈师”,听到的不再是冰冷的系统提示音,而是一段安静的、沙沙作响的白噪音。
它像一种沉默,更像一种温柔的陪伴。
一周后,数据分析师许文澜在例行报告中,紧急标红了一项异常流量。
她现,苏霓上传的那段编号为snoo的音频,在深夜时段被反复播放,流量峰值甚至过了平台最热门的付费内容。
大量用户在音频下留言:“听着这个,竟然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不是催眠曲,但比任何催眠曲都管用,好像有人在旁边陪我守夜。”
许文澜立刻对这段音频的声波频谱进行了深度分析。
结果让她大吃一惊——这段看似随意的自然录音,其白噪音的频率,竟然精准地覆盖了现代都市人群最容易产生焦虑情绪的共振区间。
它像一把无形的音梳,温柔地梳理着人们紧绷的神经。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她脑中成形。
她立即带领团队,以此为基础,紧急开了一个名为“陪伴声景”的新功能。
她们整合了城市里各种被忽略的自然音——清晨的鸟鸣、午后的蝉噪、老式收音机的电流底噪,甚至模拟出平稳的心跳声和呼吸声。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组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陪伴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