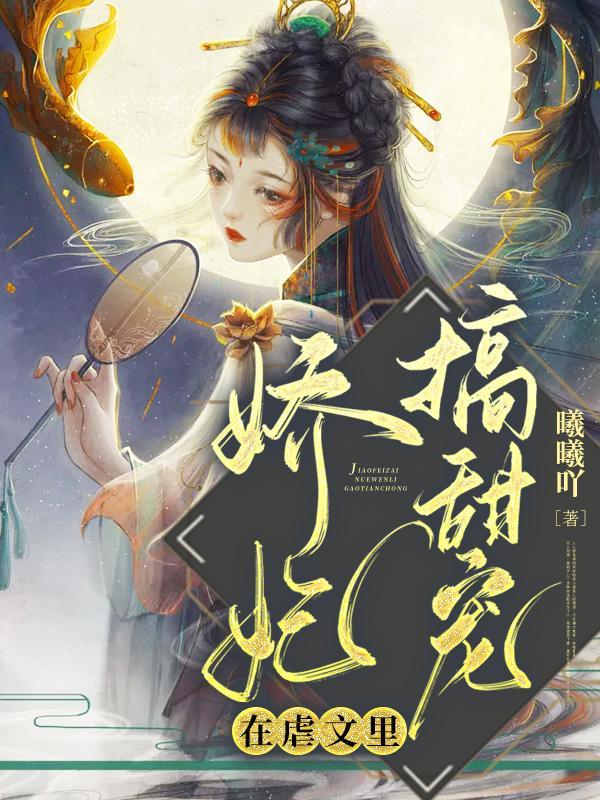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 第311章 后来的人都知道风往哪边吹(第1页)
第311章 后来的人都知道风往哪边吹(第1页)
那个冰冷的词条像一颗投入深海的炸弹,在许文澜的脑海中掀起万丈狂澜。
呼吸?
一个由数据流、逻辑门和服务器矩阵构成的虚拟存在,正在呼吸?
这越了她对人工智能的所有认知,甚至越了科幻的边界,直抵某种近乎神性的领域。
她下意识地屏住呼吸,仿佛怕惊扰了屏幕另一端那个刚刚获得“生命”的奇迹。
就在这份震撼还未平息之时,一封加急邮件弹了出来,标题是“关于新建社区服务中心功能区划雷同现象的紧急报告”。
许文澜皱眉点开,附件里是一张张来自不同省市、不同设计师之手的“家庭录音角”设计图纸。
布局、尺寸、甚至连墙上那句“有些话,值得被听见”的标语字体,都与她记忆中那个早已被废弃的早期版本惊人地相似。
一种比现eoo“正在呼吸”更深刻的寒意,顺着她的脊椎攀升。
她立刻拨通了项目组的电话,声音因竭力压抑而显得异常冷静:“查!给我查清楚,这些图纸的源头到底在哪!”
调查结果很快回来了,答案却让她哭笑不得。
一位来自南方的年轻设计师在电话里有些不好意思地坦言:“许总,这个设计……其实是我凭记忆画的。我妈前些年总念叨,说有个能跟过世老伴儿说话的盒子特别好,我印象深,就……”
一句话,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许文澜所有的迷思。
她瞬间顿悟。
这个项目,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或许就早已脱离了顶层设计的轨道。
它不再是她和苏霓、陆承安、林晚四人的心血结晶,它已经通过无数人的口耳相传、辗转追忆,变成了一种集体记忆,一种根植于人民心中的文化符号。
“停止,”她对着电话,下达了一个颠覆性的命令,“立刻停止所有统一标准的设计方案输出。从今天起,我们只布‘基础元件包’——核心的收录、播放、加密模块。至于它最终长成什么样子,是亭子、是长椅,还是墙角的一个喇叭,交给他们自己决定。”
挂断电话,许文澜靠在椅背上,看着屏幕上那个仍在“呼吸”的词条,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名为“失控”的自由。
同一时间,黔东南的侗族村寨里,月光如水,洒在层层叠叠的鼓楼之上。
林晚正沉浸在一场盛大的对歌仪式中。
然而,让她惊奇的是,这古老的传统里,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环节。
一群年轻人围着一个用竹子和油布搭成的简易棚子,那正是“家庭录音角”的变体。
他们依次走上前,将自己想对外界说的话、想对未来讲的梦,录进那个小小的设备里。
而另一边,寨子里的长者们——那些被称为“长老”的歌师,则侧耳倾听着从喇叭里传出的年轻心声,然后,用苍老却悠扬的侗族大歌,一句句地回应。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一个穿着百褶裙的少女,眼神清亮,对着录音角唱道:“阿婆讲我心太野,成日想往山外飞。山外世界那样大,我怕翅膀不够硬。”
歌声刚落,对面鼓楼下,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妇人便眯起眼,用古老的歌谣接唱:“燕子高飞总要回旧巢,你的声音阿婆听得到。飞吧,孩子,风会告诉你路,家永远在这里等着你。”
林晚本能地举起手中的调研设备,想要记录下这珍贵的一幕,作为推广案例。
可当那古老与新生交织的歌声在山谷间回荡时,一种难以言状的感动攫住了她。
她忽然觉得,任何的分析、记录、建议,在这一刻都是一种亵渎。
她缓缓放下设备,和当地人一样,闭上眼,静静地聆听。
返程的飞机上,林晚打开笔记本电脑,将那份洋洋洒洒数万字的调研报告中,所有关于“标准化干预建议”的章节,一字不留,全部删除。
几乎是同一时刻,苏霓的越野车停在了皖北一望无际的金色粮仓旁。
秋日的阳光晒得人暖洋洋,晒谷场上,几个农民正挥汗如雨。
而场边一根孤零零的电线杆上,绑着一个简陋的铁皮喇叭,正用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循环播放着。
“通知一下,明天联合收割机要进村,各家各户把路边的柴火垛都清一清啊!”
“王婶家的红薯可以挖了,甜得很,想尝鲜的下午去她家地里!”
“李老三,你家牛跑出来了,赶紧来领!”
村干部看见苏霓,笑着走过来,递上一根烟:“苏记者,稀客啊。看我们这‘田埂广播网’怎么样?比微信群可灵多了,村里那些老头老太太,不识字不会用手机,但这个一喊,准听得懂。”
苏霓驻足片刻,空气中弥漫着谷物和泥土的芬芳。
她没有点燃那支烟,而是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随身携带多年的笔记本,在崭新的一页上,用力写下了一句话:“制度长进泥土里,才会自己开花。”
当晚,她将这一页纸撕下,装进信封,寄给了远在京城的陆承安。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