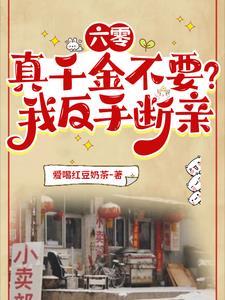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 第218章 课本锁不住的风(第2页)
第218章 课本锁不住的风(第2页)
一个特殊的请求通过加密渠道传到了她这里:一位曾在“记忆角”活动中,颤抖着讲述了自己顶替哥哥身份活下来的老人,病危了。
他临终前唯一的愿望,就是想亲眼“看”一看,自己的故事是不是真的被记录了下来。
凌晨三点,林晚带着一台便携式数据终端,冲进了重症监护室。
在弥漫着消毒水味的病房里,她在老人床前,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终端。
屏幕上,幽蓝色的光芒照亮了老人枯槁的脸。
林晚调出了那段被打上了绝密标签的录音文字档案,并点下了播放键。
“我叫李铁成,但我弟弟,真正的李铁成,在六十年前那场饥荒里,把最后一个窝头给了我……”
稚嫩清脆的童声,从终端里缓缓流出。
那是他们“记忆传承计划”的一部分,由孩子们朗读这些被记录下来的口述史。
老人浑浊的眼睛里,突然迸出一丝光亮,浑浊的泪水顺着他深刻的皱纹滑落。
他用尽全身力气,微微点了点头,枯瘦的手在旁边的纸上,颤颤巍巍地写下了两个字:“谢谢”。
写完,他的手垂落下去,呼吸监测仪上,心跳的曲线逐渐拉成了一条直线。
林晚对着老人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拿起那张写着“谢谢”的薄纸,用终端的扫描功能,小心翼翼地将其数字化。
她深吸一口气,在编号栏里,郑重地敲下了一串字符:oooo。
这是“民间记忆数字档案”收录的第一份“回执”。
而在千里之外的京城,一间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陆承安终于收到了那个他等待已久的文件袋。
来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法工委的正式通知。
他拆开封条,拿出那份厚厚的文件草案,目光直接锁定在了封面上那行醒目的黑体字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记忆保护法(草案)》。
他快翻阅,指尖最终停在了其中一章。
那里的标题是“口述历史资料的采集与保存特别条款”,内文明确规定,对于由社会组织或个人起的,以保存民间记忆为目的的非官方历史记录载体,应予以法律地位上的承认与支持。
陆承安知道,这看似简单的几行字,背后是无数次的博弈、妥协、据理力争,是无数个像苏霓团队一样的“吹风者”在体制内外共同角力的结果。
在草案的审阅确认书上签字时,他那支价值不菲的钢笔,笔尖在纸上悬停了足足十几秒。
傍晚时分,夏日的燥热渐渐褪去。
苏霓独自一人登上了电视台旧楼的天台。
这里是她三十年前,作为一名实习记者,第一次主持外景节目的地方。
脚下的城市华灯初上,远处校园的轮廓依稀可见。
手机轻微震动了一下,是许文澜来的实时地图截图。
在中国地图上,代表着“记忆角”活动点的红色光点,已经达到了个,并且还在以每分钟新增六条记忆上传的度,不断闪烁、蔓延,仿佛一片燎原的星火。
与此同时,她收到了另一条消息。
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由一群普通中学教师自编纂的《补充教材·民间记忆卷》,正悄然出现在全国多个城市的二手书市场和网络书店。
那本书的封面,是一棵冲破了龟裂土地,顽强生长的银杏树。
远处,黄昏的校园里,一面面象征着“铭记与探寻”的蓝丝带在风中飘扬。
苏霓忽然听见楼下传来一阵稚嫩的歌声。
那是一群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练着一新编的儿歌:
“小小的种子怎么芽?它要钻出泥土呀。
心里的故事怎么说话?它要自己冒出来呀。
高高的墙壁怎么倒下?风从裂缝吹过它。
被忘掉的名字怎么回家?我们把它喊回来呀……”
苏霓闭上眼,嘴角控制不住地微微上扬。
她仿佛真的看见了那股酝酿已久的风,终于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穿过了所有紧闭的门窗,吹遍了这片广袤的大地。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屏幕再次亮起,打破了这片刻的宁静。
不是团队成员的消息,而是一条来自某个官方新闻客户端的推送预览。
屏幕上弹出的那行黑色小字,瞬间凝固了天台上的晚风。
喜欢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请大家收藏:dududu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