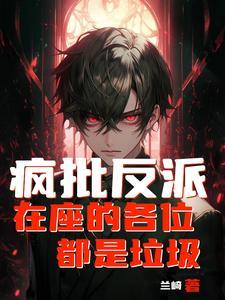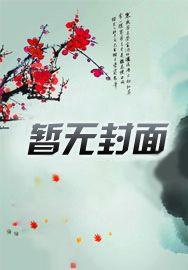SODU搜读小说>八零飒爽女主持,开局惊艳全场 > 第229章 谁在给风画路线(第1页)
第229章 谁在给风画路线(第1页)
课题启动会的空气,凝重如铅。
宽敞的会议室内,长条桌两侧坐满了各部委的代表,每一张面孔都带着审慎与探究。
声的是一位来自关键部委的代表,他双臂交叠,身体后倾,语气中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质询:“苏主任,我必须指出,你们基金会收集的这些所谓个体故事,固然令人同情,但其代表性值得商榷。更重要的是,你们到底想说明什么?难道要让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演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常态化负担吗?”
这番话像一颗投入静水里的石子,激起的却是暗流而非涟漪。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苏霓身上,等待着一场唇枪舌战。
然而,苏霓并未如他们预想般起身辩驳。
她只是淡淡地扫了那位代表一眼,眼神平静无波,随即朝身旁的许文澜递去一个指令性的眼神。
“请大家看大屏幕。”许文澜的声音清脆而冷静,瞬间将全场注意力吸引过去。
巨大的电子屏上,一幅中国地图浮现。
下一秒,无数光点在地图上亮起。
“红色光点,代表在我们项目前期试点中,已成功完成身份信息修复与确认的个体案例。蓝色光点,则代表数据库中记录在案、亟待处理的悬置案例。”
许文澜话音刚落,屏幕左下角的时间轴开始滚动。
从十年前开始,加向今天推进。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眼睁睁看着南方的几个省份,红色光点如同燎原之火,密集地爆、扩张,连成一片炽热的暖光。
然而,视线上移,广袤的北方大地,却依旧是大片深不见底的、令人心悸的蓝色沉寂。
时间轴在“今天”的位置骤然停住。
画面切换,一幅色彩斑斓的热力图取代了光点地图。
“这是根据我们数据库模型生成的全国公民身份问题‘平均等待年限’热力图,”许文澜的声音微微提高,带着不容置疑的穿透力,“颜色越深,代表该地区居民从问题出现到最终解决,需要等待的时间越长。请看这里,”她用激光笔,在图上一片深红如烙铁的区域画了个圈,“最高值,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这个数字像一枚无声的炸弹,在会议室里轰然炸开。
四十三年,足以让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长成一个鬓角染霜的中年人。
之前还带着审视态度的代表们,此刻脸上只剩下愕然与震撼。
那位问的代表,身体不自觉地前倾,嘴唇微张,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片深红,正是他分管的区域。
会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中央空调的微风还在固执地吹拂。
许文澜抓住这宝贵的寂静,利落地切换了下一页演示文稿。
“在此,我们正式布期《公民身份可及性指数报告》。”她语气一转,充满了学术的严谨,“我们选取了人均gdp、常住人口流动率、历史档案数字化水平、基层行政效率、教育资源公平性以及法律援助覆盖率,共六项核心指标,构建了我们的评估模型。”
屏幕上,复杂的公式和图表一闪而过,最终定格在一张结论图上。
“结论非常清晰:身份修复严重滞后的区域,与社会综合治理的薄弱地带,呈现出惊人的高度重合。这不是历史负担,”许文澜的目光越过众人,直视那位问的代表,“这是展短板。”
会议结束后,在返回基金会的车上,许文澜将一叠厚厚的报告递给苏霓,她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数字不会撒谎,但它会站队——只要我们让它站在对的一边。”
苏霓接过报告,指尖在封面上轻轻划过,没有说话,但嘴角那抹微不可察的弧度,已是最好的肯定。
风暴的中心平静下来,外围的涟漪才刚刚开始扩散。
赵小芸接到了苏霓的秘密指令。
她的任务是即刻动身,回访三位曾在项目听证会上为自己或家人权益激烈声的当事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修复之后”的生活。
镜头下,那位曾因儿子的“黑户”身份而当众落泪的母亲,此刻正满脸笑容地为儿子收拾行囊。
一张崭新的户口簿和一张定向医学生的录取通知书,被她小心翼翼地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少年看向镜头的眼神,不再是过去的躲闪与自卑,而是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另一位曾因工龄计算错误而养老金被克扣多年的老人,在领回了数万元的差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镇上最好的石匠铺,为自己和已故的老伴,订了一块厚重光洁的新墓碑。
赵小芸的镜头远远地拍着,老人用粗糙的手,一遍遍摩挲着碑上刚刚刻好的名字,口中喃喃自语,像是在与另一个世界的人分享这份迟来的慰藉。
赵小芸将这些没有一句解说、没有一句旁白的纯粹影像,剪辑成一部名为《修复之后》的短片。
它没有公开布,而是通过加密渠道,精准地送到了参与此次课题的五位司局级官员的私人邮箱中。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沉默的影像,比任何激昂的报告都更具力量。
次日上午,苏霓就接到了电话。
电话那头,正是五位官员中的一位,他主动提议,应当在课题中增设一个“成效追踪与社会影响评估”的子项目,并表示愿意牵头协调资源。
苏霓挂断电话,看着窗外。她知道,坚冰已经从内部开始融化。